最近,時代論再次成爲了新聞焦點。有許多教導「被提」「敵基督已經兵臨城下」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議都是虛假的」(還有更多和末世相關的預言)的牧師們紛紛就 2023 年 10 月 7 日開始的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是否已經被聖經預言了發表看法。這包括了羅伯特·傑弗里斯(Robert Jeffress)和格雷格·勞里(Greg Laurie)這樣的知名大教會牧師,也包括了上百位不太知名的傳道人。
在人們對中東問題興趣高漲的時候,福音派的局外人(包括許多福音派信徒)會覺得,這種流行的對地緣政治的「聖經預言」就是福音派的共同觀點。當然,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大多數知情的時代論基督徒)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神學對美國福音派的影響程度和侷限性呢?
我最近出版了《時代論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Dispensationalism)一書,所以我應該對這個話題有資格發表一些看法。書名中的「衰」一詞,乍一看似乎與最近流行的和講壇上的末日論嘮叨相矛盾。一些關鍵的定義和區別將幫助我們釐清已經多變的福音派神學中複雜和潛在的混亂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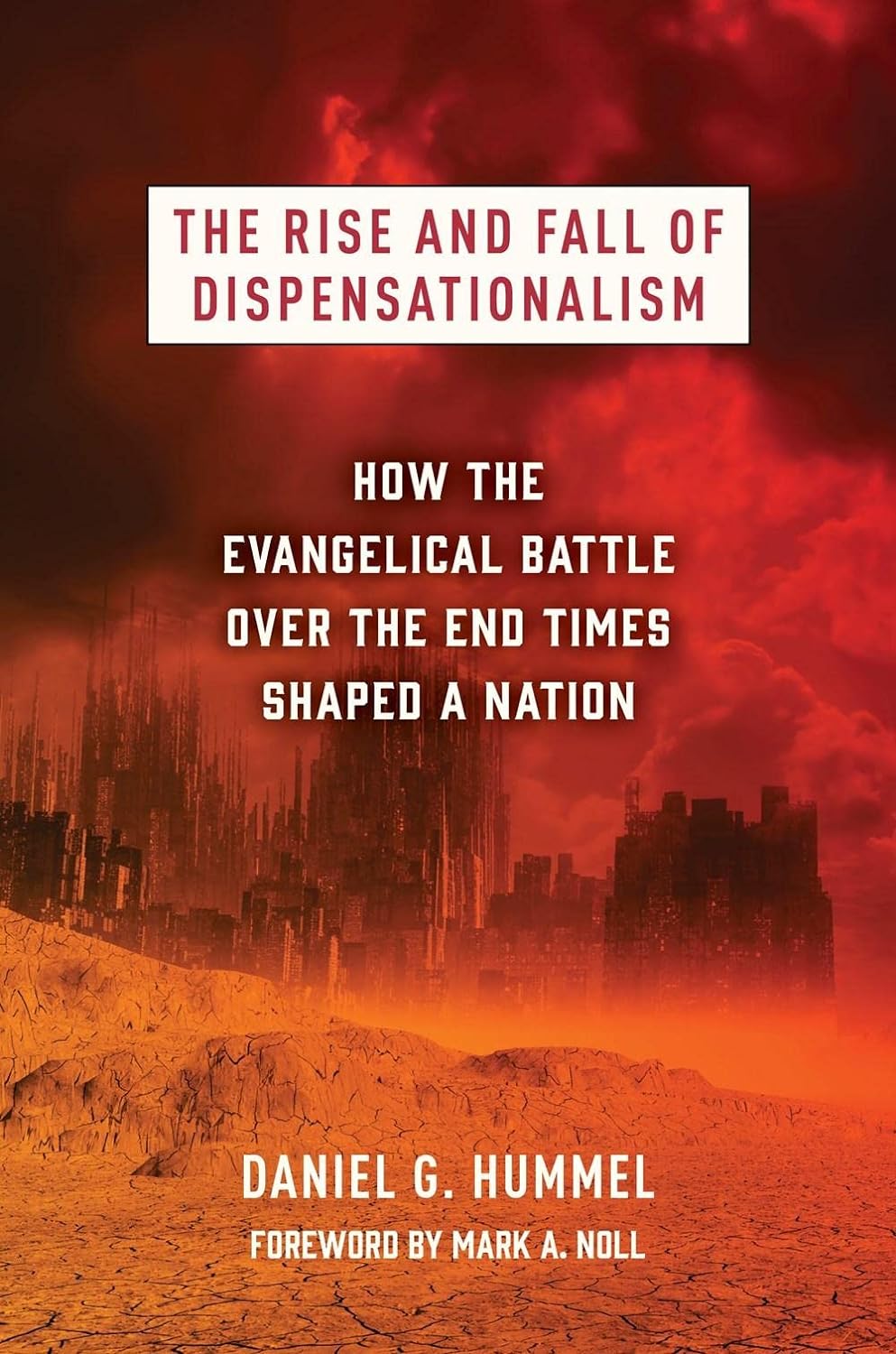 首先,儘管末世論神學最受關注(而且,無可否認,也是媒體報導中最廣爲人知的部分),但時代論遠不止是末世論。它是一個強大的神學體系,基於一套特定的解經方法,影響著基督徒對教會生活和社會中許多問題的態度。其獨特的末世論擁有廣泛的接受者,但它的其他核心教義也對解經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教會與以色列的區別以及神國的未來定位。
首先,儘管末世論神學最受關注(而且,無可否認,也是媒體報導中最廣爲人知的部分),但時代論遠不止是末世論。它是一個強大的神學體系,基於一套特定的解經方法,影響著基督徒對教會生活和社會中許多問題的態度。其獨特的末世論擁有廣泛的接受者,但它的其他核心教義也對解經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教會與以色列的區別以及神國的未來定位。
其次,今天的時代論有兩大流派,這兩個流派都值得討論。兩者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其一是學術派時代論(scholarly dispensationalism),這一流派更多的是在一些神學院、基督教大學和少數教會中得到討論和教導,但其在福音派中的支持者和影響力相對較小,相比前幾代人而言我們可以說這一流派的影響力已經式微。
還有一個流派則是流行時代論(popular dispensationalism),其主要觀點激發了書籍、電視、電影、音樂和其他媒體的靈感。一些教會——包括大型教會——以及福音派政治圈子尤其熱衷於討論這一流派。我們可以稱之爲「流行時代論」("pop-dispensationalism"),這也是大多數美國人最熟悉的版本,例如《末世迷蹤》(Left Behind)系列小說和電影,以及類似於好萊塢喜劇電影《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中的末日神學。
當然,學術派時代論和流行時代論之間有重要的聯繫,但在風格、方法、可信度和實質內容上也有很多不同之處。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些區別,我們就無法準確理解時代論對美國福音派的影響。
查爾斯·瑞裡(Charles Ryrie)的《今日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 Today,出版於 1965 年)主要討論的是 20 世紀 60 年代的學術派時代論。基於這本書的形式,我們將對當下(2024 年)的時代論進行一次簡短的概述。本文將簡單描述學術派時代論與流行時代論之間的辯證關係,這種關係在 1965 年的時候還不那麼突出。
流行時代論繼續在多種場合、通過多種形式的媒體爲數百萬基督徒的神學和屬靈生活提供背景知識。以圖書出版爲例,美國亞馬遜「基督教末世論」(Christian eschatology)這一子類型的暢銷書排行榜顯示,受時代論啓發而對現代政治進行分析的著作高居榜首。大衛·耶利米(David Jeremiah)、阿米爾·察爾法提(Amir Tsarfati)和喬納森·卡恩(Jonathan Cahn)的書經常名列前茅,托馬斯·耐爾森(Thomas Nelson)、貝克(Baker)和丁道爾(Tyndale)等大型出版商也在出版此類書籍。
在其他媒體中,流行時代論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有電視佈道家(羅伯特·傑弗里斯和 2023 年去世的查爾斯·史丹利)和聖經廣播(約翰·麥克阿瑟、查克·斯溫道)等等。2023 年,《末世迷蹤》系列電影又增加了一個新成員,這次的導演居然是凱文·索伯(Kevin Sorbo)。
值得反思的不僅是這些作品的數量和影響力,還有其質量。在這方面,情況就不那麼令人印象愉快了。許多暢銷書都是無休止的分析和預測,這可能會對讀者產生扭曲的精神影響。
與 20 世紀 70 年代的前輩(如哈爾·林賽 [Hal Lindsey] 的《晚期偉大地球》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等書籍和《夜行神偷》 [A Thief in the Night] 等電影)一樣,此類作品所呈現的末世論與時代論神學嚴重脫節。幾十年來,許多深思熟慮的時代論神學家一直對此表示遺憾,但這並沒有阻止這一滑坡潮流。
與它的前輩不同,今天的流行時代論也受到福音派文化和社會吸引力的高度拉扯。20 世紀 70 年代的時代論人士聲稱要把福音信息傳給非基督徒(雖然他們把大眾對流行末世論的迷戀作爲傳福音的工具,但這是有問題的),毫無疑問在許多情況下也取得了成功,但現在的流行時代論並沒有試圖扮演這一角色。它的產品針對的是現有的福音派信徒,並向他們推銷自己的產品。
流行派時代論的問題在今天日趨嚴重,因爲其商業化和受消費者驅動的發展進一步使其遠離了學術派時代論。
即使在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學術派時代論影響最盛的時候,這兩者也曾出現過緊張關係,但尤其自那以後,它們就漸行漸遠。這既是因爲該教義受到了福音派神學和聖經研究學者中歷史主義者越來越多的審視,也是因爲許多曾對時代論深信不疑的機構拋棄了該神學。
雖然時代論在基要主義者或福音派中從來都不是唯一的神學傳統(還有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無千禧年加爾文主義或喬治·埃爾登·賴德 [George Eldon Ladd] 的歷史性前千禧年),但到了 20 世紀 50 年代,時代論已成爲占主導地位的神學範式之一。它擁有一大批穩定的神學院和大學,以達拉斯(DTS)、泰爾博特(Talbot)和恩典(Grace)這三家分別位於美國三個不同地理和文化區域的代表性時代論神學院不斷壯大,時代論知名神學家們也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從 20 世紀 40 年代的奧斯瓦爾德·T. 艾利斯(Oswald T. Allis)和 20 世紀 50 年代的賴德(Ladd)等批評家開始,該教義的保守反對者在神學、聖經和知識方面不斷提出並擴大批評。再加上從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到 N. T. 賴特(N. T. Wright)的英國批評家,以及近幾十年來五旬宗和美南浸信會學術界對時代論的反駁,時代論在當今神學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比上世紀任何時候都要小得多。
與此同時,這一神學曾經穩固的大本營也已經擺脫了歷史上時代論對其的影響。像拜奧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這樣離開時代論的例子在基督教神學院和大學界隨處可見。拜奧拉大學由魯本·A. 託雷(Reuben A. Torrey)和威廉·E. 布萊克斯通(William E. Blackstone)等時代論信徒於 1908 年創建,如今它所受的時代論影響已經很淡薄了,在某些地方甚至完全沒有時代論的影子。
最近的另一個離開時代論的代表機構是穆特諾瑪大學(Multnomah University),它曾是一所聖經學院,也是在其長期校長威拉德·奧爾德里奇(Willard Aldrich)領導下進行時代論神學研究和教育的中堅力量,現在被歸入傑瑟普大學(Jessup University),成爲後者的一個分校區。此外,一些宗派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美國播道會(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EFCA,曾是一個堅定的前千禧年主義和深受時代論影響的宗派)於 2019 年從其信仰聲明中刪除了「前千禧年」一詞。
雖然如此,這一教義的「衰落」仍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包括邁克爾·弗拉赫(Michael Vlach)、邁克爾·J. 斯維格爾(Michael J. Svigel)和科里·馬什(Cory Marsh)在內的時代論專業學者繼續出版神學、聖經研究和歷史方面的學術著作。帕特諾斯特出版社(Paternoster Press)和 SCS 出版社(SCS Press)等中小型出版社也在出版倡導時代論的書籍,學術派時代論學者參加了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ETS),並維持著自己的小型網絡。
這兩種發展——淺薄的、神學不足的流行時代論大肆流行和學術派時代論的衰落——是我所說的這一教義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衰落」的實質。然而,衰落既不是死亡,也不是消失。儘管今天它的影響有好有壞,但它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至少在紙面上,仍有一些神學院和學校堅持這一神學。其中包括達拉斯神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和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它們是美國最大的兩間培養牧師的跨宗派機構。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神學院,如南加州神學院(Southern California Seminary)、馬斯特斯神學院(The Master's Seminary)和牧人神學院(Shepherd's Theological Seminary),也都致力於時代論特色,像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這樣的本科院校也仍然在這一陣營中。
然而,具體觀察每一間院校,我們不難發現學生們所接受和神學院所教導的時代論「濃度」不一。有的機構很明確肯定時代論,有的機構含糊其辭,有的甚至隻字不提。此外,時代論的主張者承認很難得到主流學術出版商和學術期刊的關注,這就進一步限制了學術性時代論在高等教育內外的影響力。
近幾十年來,組織和擴大福音派事工中規模最大、最具新聞價值的運動中,明顯時代論是缺席的。不僅如此,許多運動還對時代論充滿敵意。當然,我們應當意識到這些運動在與福音派歷史性神學有著各不相同的連續性,但它們都是當今的重要運動,它們揭示了福音派世界的組織能量集中在哪裡。
追溯到 20 世紀 90 年代,新興教會運動(Emergent Church)、「年輕、躁動的改革宗」「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專注於傳福音、社會正義和社區參與——譯註)、基督教國族主義、紅字基督徒(Red Letter Christians,強調遵從耶穌關於社會正義的教導——譯註)等等,都對時代論神學提出了批評——而且理由各不相同。與 70 年前相比,當時的全球宣教運動、青年和大學事工運動,以及(幾十年後的)耶穌子民運動和彌賽亞猶太教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時代論及其神學的推動。
或許,在福音派更廣泛的群體中,時代論仍然具有領導地位的一個領域就是捍衛聖靈恩賜終止論(cessationist)觀點。麥克阿瑟和賈斯汀·彼得斯(Justin Peters)這兩位信徒在這方面很受歡迎。但在美國和全球範圍內,這一神學立場正受到來自五旬宗和非五旬宗基督徒越來越大的壓力。
綜合來看,這些軌跡表明,在美國福音派中,時代論的發展勢頭正在衰退,儘管這種衰退的原因極其複雜。
雖然流行時代論在商業和消費領域的成功令人驚歎,但它過去的一個關鍵影響領域卻在減弱:受到教會支持的政治家。
20 世紀 20 年代,威廉·貝爾·萊利(William Bell Riley)和 J. 弗蘭克·諾里斯(J. Frank Norris)等人向進化論和酒精發起了戰爭。20 世紀 50 年代,約翰·賴斯(John R. Rice)、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和J. 弗農·麥基(J. Vernon McGee)擁有全國最大的批評共產主義的平台。20 世紀 80 年代,傑里·法威爾(Jerry Falwell)和蒂姆·萊希(Tim LaHaye)帶頭反對世俗人文主義。這些人都相信或非常認同時代論。
今天,雖然仍有著名的時代論牧師參與政治(傑弗里斯和約翰·哈吉,或約翰·麥克阿瑟對新冠政策的批評),但保守福音派政治的重心已轉向其他方向。20 世紀 80 年代,對這一教義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是新近大肆鼓吹的後千禧年「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m"),如今,這種「重建主義」在日益壯大的後千禧年國族主義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道格·威爾遜(Doug Wilson)是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早年曾是一位時代論者。他從這一神學中「轉型」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他所代表的保守改革宗後千禧年主義在西北太平洋地區和其他地方的發展是更大神學趨勢的標誌。
與改革宗後千禧年主義相比,美國基督教政治領域受五旬宗影響更具現實意義。寶拉·懷特(Paula White)等人曾擔任川普(Donald Trump)的顧問,而哈吉(Hagee)則管理著美國最大的親以色列宣傳團體——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組織(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
哈吉將一種改良後的末世論(他出版了大量流行末世論書籍)與五旬宗和成功神學結合,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混合體,吸引著不同的支持者和不同動機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哈吉的影響使他成爲美國與全球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網絡溝通的橋樑,而全球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網絡絕大多數是五旬宗和成功神學人士(尤其注重《創世記》12:3),並在神學上的關鍵部分反對時代論。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很難想像當今國際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在實質和言辭上都反對時代論這一教義。
懷特則更接近於統治神學的立場,呼籲基督徒在社會和文化中行使權力。就政治議題而言,這一觀點——以及全球五旬宗和靈恩派「網絡」基督教的觀點——更多地與保守的改革宗後千禧年主義相一致,而不是與時代論一致,如今,它爲福音派政治組織提供了大量能量。
上述四點描繪出了當今時代論的複雜圖景,橫跨學術、文化和政治領域。我們無從知曉這一教義在未來50年中究竟會如何發展,但如果它確實在福音派神學院中重獲影響力,或抓住了Z世代福音派信徒的想像力,那將是對當前趨勢的顯著逆轉。
與此同時,如果時代論失去商業吸引力,這也會成爲新聞,而且很可能標誌著福音派文化發生了更廣泛的鉅變——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在福音派文化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末世論正在淡化和逝去。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4 Snapshots of Dispensationalism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