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基督徒普遍反對把福音書「去神話化」(demythologization),例如,他們反對將耶穌的復活解釋爲對新生命原則的神話式比喻。福音派強烈主張復活的歷史性至關重要。然而,一旦論及聖經人物亞當和夏娃,他們卻往往更願意視之爲神話或象徵。
本文的目的簡單明了。我想要說明:對基督徒而言,相信亞當是一個歷史人物、是全人類的祖先,這並非字面解經者的吹毛求疵,而是符合聖經的,神學上也是必要的。
文本證據
創世記前幾章有時使用 'ādām(亞當)一詞來表示「人類」這一普遍概念(如創1:26-27),且因這些章節明顯具有文學結構,有人便將亞當這一形像視爲文學手法而非歷史事實。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必須作出選擇嗎?縱覽全本聖經,我們發現使用文學手法展現歷史事件的例子屢見不鮮:想想福音書描述尼哥底母夜間來見耶穌,或強調耶穌死時恰逢逾越節。多數解經者樂意承認,聖經作者會使用文學手法,以凸顯所述歷史事件的神學意義,引起我們的注意。「文學」(literary)表述並沒有排除「字面含義」(literal)的準確性。
接下來的問題必然是:在亞當的例子裡,將其看爲「文學」手法是否排除了它的「字面含義」呢?聖經中提及亞當的其他經文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創世記第5章、歷代志上第1章及路加福音第3章記載的家譜均追溯至首位父親亞當——儘管聖經家譜有時出於種種原因略去人物姓名,但從未添加虛構或神話人物。耶穌教導婚姻真理(太19:4-6),或猶大在猶大書第14節提到亞當時,並未特別說明什麼來表示說亞當並不是歷史人物,他們並不認爲亞當與其他舊約人物有所區別。保羅談到「先造的是亞當」、「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林前11:8-9;提前2:11-14)時,也必須假設創世記第2章記載了歷史事實。如果他意指亞當和夏娃不過是神話象徵,代表了男人先於女人存在的永恆真理,那麼他的論證就成了胡言亂語。
神學必要性
我們可將上述經文視爲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說明聖經作者認爲亞當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間接證據十分有用,也非常重要,但我們還有更具說服力的證據。亞當在保羅神學中的角色,使亞當的歷史真實性成爲福音基本敘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確實如此,亞當的史實性就並非細枝末節,而是構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礎。
第一個例證來自羅馬書5:12-21:保羅將「一人」(亞當)的罪,與「一人」(基督)的義做了對比。使徒保羅認爲,儘管單數「子孫」(seed)和複數「眾子孫」(seeds)差別細微,但仍有必要做出區分(加3:16),因此我們大可認爲,他不會由於粗心大意,將「眾人」寫作「一人」。事實上,保羅多次以「一人」對比眾人,而「獨一性」(oneness)恰恰鞏固了保羅的觀點,即一人(基督)的一次救恩,塗抹了一人(亞當)的一次過犯。
整段經文中,保羅以談論基督的方式談論亞當(他說死是「因」亞當入了世界,在加拉太書第3章也用類似的說法,談到萬國「因」亞伯拉罕得福)。他能夠談及這「一人」犯罪以先、沒有「罪」也沒有「死」的時光,也能夠談到犯罪以後、自亞當起至摩西止的時期。保羅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他認爲亞當與基督、摩西(和亞伯拉罕)一樣,都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不僅保羅的語言表明,他相信歷史性的亞當,他的整個觀點都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如果他將歷史人物(基督)與神話或象徵人物(亞當)進行對比,那麼他的邏輯便無法成立。如果亞當和他的罪不過是象徵,歷史性的補贖自然毫無必要;消除神話性的墮落,僅需神話性的補贖。如果亞當只是神話,那麼基督倒不如單單成爲神聖寬恕與新生的象徵——這樣邏輯還更通順。然而,保羅的故事裡,罪、過犯和死進入了受造界,這是一個歷史性問題,需要歷史性的解決方案。
挪走亞當犯罪的歷史性問題不僅將導致十字架與復活的歷史性解決方案不合邏輯,更會使保羅的福音面目全非。罪與惡從何而來?若它們不是一人悖逆的結果,那麼似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罪事先存在,而惡是神造物的組成部分;要麼罪是個人主義的,幾乎從無到有由各人帶入世界。前者的一元或二元論否認了良善的造物主和其美好的造物,這顯然不屬於基督教的立場;後者近乎伯拉糾主義,即好人因模仿亞當而犯罪(並以此類推,因模仿基督而稱義)。
歷史性亞當在保羅神學中居基礎性地位,第二個例證來自哥林多前書15:21-22及45-49。保羅再次揭示了一組嚴密的對照:死因首先的人亞當而來,第二亞當或末後的人基督則帶來新生。再一次,保羅用描述基督的方式描述亞當;再一次,他將亞當視爲死亡的開端,而將基督視爲生命的源泉。
保羅寫作哥林多前書時,哥林多基督徒有關死後身體問題的長期爭論正達頂峯。爲提供終極答案、解決這一牧養問題,保羅通過展示耶穌肉身復活的歷史事實,使他們確信未來肉身的復活。耶穌復活的歷史真實性是他這一回應的關鍵。既然如此,若保羅認爲亞當是神話人物,卻仍將其與基督相提並論,就愚蠢至極了。若這二者可以並列,那麼基督的復活也可作神話解釋,而保羅的整封書信也將隨之失去重點、意義和衝擊力。
如果我在上述段落中準確表達了保羅神學,那麼一旦將歷史性亞當從保羅的福音信息中拿走,這一信息必然受損。拿走歷史性的亞當將使福音「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導致惡的起源需要另一套解釋,而處理惡的問題,也由此需要另一套救贖方案了。
是否存在第三條進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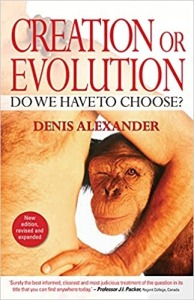 通過對約翰·斯托得 (John Stott)所著《見證基督》(Understanding the Bible,英文版49頁)中某個理論的闡釋,丹尼斯·亞歷山大(Denis Alexander)提出,傳統觀點堅持歷史性的亞當,反對者則認爲歷史性的亞當在科學上站不住腳,但第三條進路能夠避免上述兩種觀點的尖銳對立(9-10頁)。這第三條進路就是:我們雖絕對應當視亞當爲歷史人物,但並不必相信他是首先的人。根據亞歷山大所說的模型,大約200,000年前,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誕生;50,000年前,語言出現;隨後,約6,000到8,000年前,神揀選了一對新石器時代的農夫農婦,並首次向他們啓示自己。由此,神構建了「神人」(Homo divinus)——首批認識祂、靈裡充滿活力的人類。
通過對約翰·斯托得 (John Stott)所著《見證基督》(Understanding the Bible,英文版49頁)中某個理論的闡釋,丹尼斯·亞歷山大(Denis Alexander)提出,傳統觀點堅持歷史性的亞當,反對者則認爲歷史性的亞當在科學上站不住腳,但第三條進路能夠避免上述兩種觀點的尖銳對立(9-10頁)。這第三條進路就是:我們雖絕對應當視亞當爲歷史人物,但並不必相信他是首先的人。根據亞歷山大所說的模型,大約200,000年前,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誕生;50,000年前,語言出現;隨後,約6,000到8,000年前,神揀選了一對新石器時代的農夫農婦,並首次向他們啓示自己。由此,神構建了「神人」(Homo divinus)——首批認識祂、靈裡充滿活力的人類。
誠然,這一綜合進路頗具創意,它巧妙地繞開了因拒絕歷史性亞當導致的神學鴻溝,但也爲自身創造了不少重大問題。首先,應如何看待亞當的同輩。亞歷山大說,前述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遍滿全地,已達數萬年之久。他明智地避免將其理解爲低人一等的生物,並強調「全人類,包括新石器時代活在世上的其他數百萬人,都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無一例外」(238頁)。如果不這麼說,他將陷入尤其糟糕的泥潭:據他本人稱,亞當夏娃誕生以先,澳大利亞原住民已經存在了40,000年——他們將淪爲非人動物。亞當夏娃的父母作爲非人動物,想必也將與這些原住民一起,成爲飢餓「神人」正當的食物來源。
爲避免上述情形,亞歷山大的觀點滑向了更危險的領域。他在解釋亞當夏娃與其同輩的分別時,便已跨出了重要一步。他提出,亞當夏娃誕生之前,已有大量新石器時代人按照神的形像被造。將亞當夏娃分別出去、成爲「神人」的事件,僅僅是「通過神對亞當和夏娃的啓示......他們清楚明白了神之形像的現實意義」(238頁)。那麼,亞當和夏娃並非按照神形像新造的;他們出生便已帶有神的形像,是一長串神之形像承載者的後裔。不同的是,他們現在明白了其中的意義(與神的個人關係)。
上述觀點的第一個問題在於聖經根據。創世記第1和第2章特別指出,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是亞當和夏娃(創2:18-25重述了創1:27展示的事件)。經文並沒有說,某些生物按照神的形像被造,而此後他們的後代才理解這一點。恰恰相反,創世記2:7似乎可作爲例證,強調亞當的受造是直接的、特殊的創造行爲。若該問題可以克服,隨之而來的神學問題恐怕無法逾越,即,如果人類在亞當夏娃以前已經具有神的形像,那麼我們僅剩兩種選擇:或者在亞當夏娃之前,還有一個首先的人被賦予了神的形像——這樣我們便有了兩個亞當,一個是首先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生物,一個是承載神的形像並首先理解其含義的人亞當;或者,若神的形像會隨人類發展緩慢進化,那麼我們便會看到一系列承載神之形像的人類始祖,和多個亞當。
上述觀點不僅極不自然,也將滾雪球般迅速導致一系列後果。若正如亞歷山大所言,具有神的形像是指與神建立個人關係,那麼所有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人,只要尚未接受啓示、了解其中含義,就一定是在犯罪。他們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目的,正是與神交通,而他們與神並無往來。儘管並未言明,亞歷山大描繪的,實際上是沉溺於偶像崇拜的人類。因爲他說:「在此(亞當夏娃的)時代之前,宗教信仰已然存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尋求上帝或諸神,以各種方式解釋自己生命的意義。」(237頁)因此,在該觀點模型下,人類墮落之前就已有了罪。
假設神忽略了上述罪行(儘管理由我們不得而知)。但若祂如此行事,便與保羅在羅馬書1:18-32中所言相悖。保羅解釋道,神的忿怒顯明在一切(不義的)人身上,並非因爲人類未曾留心神對「按著神的形像被造」含義的特定啓示,而是因爲人們拒絕承認,創世以來,神在所造之物中的啓示是明明可知的。事實上,根據羅馬書1:18及其後經文,亞歷山大筆下信奉宗教/崇拜偶像、生活在亞當之前的智人必定落在神的忿怒之中。即使羅馬書第一章的內容能夠與該模型調和,神的做法也相當奇怪,因祂竟爲罪和拜偶像創造機會,卻並未像之後對待亞當那樣,提供行義和真正認識神的機會。
亞當本人呢?他蒙揀選接受啓示,了解「按著神的形像被造」的意義,那時他已經有罪了。他受造本是要與神交通,然而他並未如此行事。那麼他是暫時被判無罪嗎?或者他始終有罪,只不過在創世記第三章,他首次故意犯罪?如果後者成立,那爲何亞當先前無意識的犯罪可以獲得饒恕,而後文又提到即使是無意識的犯罪也會帶來罪咎(利5:17;詩19:12)?
神在爲我們創造認識祂的機會以前,就創造了犯罪的機會——這一點反映了上述理論最令人困擾的地方,即理論中的神不知何故受制於不甚理想的環境。縱覽整套觀點,人們會覺得,其中的神不得不按照他人的規則做工,彷彿身處他人的宇宙一般。
亞歷山大針對女性受造的經文註釋清楚地體現了這一問題。根據他的說法,夏娃並非是由亞當的肋骨造成的,她與亞當一樣擁有人類父母。他認爲,創世記2:21的寫作目的在於肯定男女互補(male-female complementarity)(197頁)。毫無疑問,該段經文包含這一目的,但既然他將創世記2:21視爲神話/象徵,他也便無法在任何本體論現實基礎上構建男女互補關係。若夏娃擁有獨立於亞當的身體起源,那麼儘管神可能出於神祕的理由意圖肯定男女互補,祂並沒有本體論的基礎。換言之,祂此處的確認(以及祂在別處表達的肯定,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我們不得不如此推論)獨立於現實存在。總之,神憑空捏造了一套神學。然而,一位被迫將意義賦予本身不具意義的事件(或未發生的事件)的神,並不像至高的造物主。
最後,亞歷山大的理論模型迫使他以特定的方式解讀創世記文本。這種解讀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把圓釘插入方孔。女人的受造再次成爲絕佳的案例:「亞當認出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時,不僅認出了一個智人同類——當時周圍有許多這樣的同類——而是認出了一位信徒同工」(237頁)。該解讀不僅忽略了文本的具體內容(聖經後文引用了該段經文,可參見林前6:16-17及弗5:28-31,因此該具體內容十分重要),而且無法解釋前文爲亞當尋找「幫助者」的意義。如果創世記2:18-20表明了什麼,那就是當時沒有亞當的其他同類在場。如果僅僅尋找另一位信徒,爲何要在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中尋找呢?又爲何不提被帶到亞當面前的人類?難道神不能簡單地向周圍的智人啓示「神的形像」的意義,從而催生出所需的「幫助者」嗎?
類似的邏輯導致了他對創世記6:2的解讀。該節經文中,神的兒子們與人的女子通婚。在亞歷山大看來,情況十分簡單,即擁有活潑屬靈生命的亞當後裔與同時代的智人通婚,而這些智人沒有接受上帝的啓示,因此靈裡已死。相關教訓也很明顯:「不要與不信的人結合」,因爲「很顯然,正如6:5及後文對洪水的描述,神的審判將隨之而來」(199頁)。然而,如果創世記第6章與敬虔者嫁娶亞當血脈之外的不信者有關,那麼當「敬虔的」該隱娶了亞當血脈以外的女人作妻子時,爲何洪水的審判並未如亞歷山大認爲的那般降臨(241頁)?
我的建議是,儘管不失獨創性,亞歷山大的「第三條進路」堅持了歷史性的亞當,但並不相信他是首先的人,因此無法爲創世記文本提供前後一致的解讀。這一理論導致的神學問題,遠遠超過其解決的部分。其中一些問題(如對創世記第6章的解讀)無疑很小,僅僅表明他的理論模型缺乏內部連貫性,且與聖經記載存在出入。其他問題(如他對神作爲全能造物主的理解)則極爲嚴重,以致他的論點幾乎無可救藥。
亞當是人類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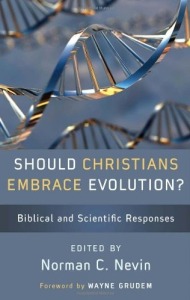 針對亞當與其他人類關係的爭論總是趨於回歸奧古斯丁與伯拉糾之間的長久論戰。伯拉糾並未質疑亞當與其他人類間的血緣聯繫,但他認爲,這一聯繫與救恩幾乎完全無關。根據伯拉糾的說法,救贖與詛咒自始至終由個人決定:一個人受詛咒,並非因其潛在地連於亞當,而是因其模仿亞當犯罪;同理,一個人得救,並非因其潛在地連於基督,而是因其模仿基督行義。換言之,救贖和詛咒不在於一個人是否獲得與亞當或基督相同的身份,而在於一個人希望分享何種命運——亞當的或基督的,並做出相應模仿。奧古斯丁回應道,首先這根本無法與羅馬書5:12-21互相協調。羅馬書指出,眾人因亞當的罪而被定罪,因基督的義而被稱義。根據奧古斯丁對保羅書信的理解,神通過兩人處理全人類的問題:亞當——首先的人、人類的頭;基督——神新造的人中的首位和頭領。
針對亞當與其他人類關係的爭論總是趨於回歸奧古斯丁與伯拉糾之間的長久論戰。伯拉糾並未質疑亞當與其他人類間的血緣聯繫,但他認爲,這一聯繫與救恩幾乎完全無關。根據伯拉糾的說法,救贖與詛咒自始至終由個人決定:一個人受詛咒,並非因其潛在地連於亞當,而是因其模仿亞當犯罪;同理,一個人得救,並非因其潛在地連於基督,而是因其模仿基督行義。換言之,救贖和詛咒不在於一個人是否獲得與亞當或基督相同的身份,而在於一個人希望分享何種命運——亞當的或基督的,並做出相應模仿。奧古斯丁回應道,首先這根本無法與羅馬書5:12-21互相協調。羅馬書指出,眾人因亞當的罪而被定罪,因基督的義而被稱義。根據奧古斯丁對保羅書信的理解,神通過兩人處理全人類的問題:亞當——首先的人、人類的頭;基督——神新造的人中的首位和頭領。
爲何亞當的身份及其與他人關係的問題會不斷回歸奧古斯丁-伯拉糾論戰?原因似乎有二:(1)該論題十分基礎,不可避免,因爲它代表了基督教福音與另一套理論間的分歧,後者採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神與救恩;(2)即使是最複雜的現代構想,也仍未脫離該辯論的基調。例如,有人認爲亞當和夏娃實際上是一群(可能是新石器時代的)人的象徵。罪在其中出現,並蔓延至全人類。此處,伯拉糾主義的問題被簡單地從大部分人類轉移到了少數原始人身上,這些原始人生活的時代是如此古早,以致前述問題看似可以忽略不計。
奧古斯丁-伯拉糾論戰的基礎似乎很難迴避。否認亞當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頭」,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導向對個體命運的個人主義解釋。個人自覺自主的程度越大,就越傾向於將基督視爲榜樣而非救主。
本體論根基
再一次,丹尼斯·亞歷山大在其理論中精明地避免了此類陷阱。儘管他非常清楚承認亞當作爲舊人之首的神學必要性,他提出了一種不同的方式,將前述神學事實與自己的觀點——亞當不是首先的人——相結合。他的做法很簡單,即將亞當作爲人類元首的法律或行政地位與亞當作爲人類自然元首或始祖的觀念分開。那麼,在某個特定時刻,神任命亞當爲頭領,不僅是每個「神人」的頭領,也是每個智人的頭領。由此,亞當首次(有意)犯罪時,神可以將這罪歸咎於每個智人,不管他們是否與亞當缺乏本質聯繫。那時,尚未獲得啓示的澳大利亞智人(這裡以先前提過、與亞當的新石器時代社區無關的族群作爲例子)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了。
然而,亞歷山大將亞當行政性的領導地位與他在自然和血緣上的領導地位分開,使同樣的問題再次出現。首先,神仍然做出了沒有本體論基礎的神學確認。亞當被任命爲人類的「頭」,而在物質現實中並非如此。因此,神將罪歸咎於毫不知情的澳大利亞原住民,這一做法似乎相當武斷。亞當與地球另一端的智人之間毫無聯繫,因此神宣佈他們應當分擔亞當的罪咎,將完全出於一時興起。
然而,聖經中的元首概念並非如此。聖經中特別提到,神對個人的審判如何影響其後代(因此舊約聖經充滿了家譜)。相關案例不勝枚舉,我們只要看看神對亞伯拉罕、雅各和大衛的祝福,或對約雅斤詛咒如何影響他們各自的後代就瞭然於心。從相反的角度,人們認爲利未「藉著」亞伯拉罕(納了十分之一),是因爲他「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來7:9-10)。換言之,個人的元首地位或總體性質從來不會與實際聯繫相脫節。
如果我們要從如何「在亞當裡」出生的討論轉向對基督徒如何「在基督裡」的研究,那麼實際聯繫就顯得尤爲必要。新約聖經中,基督徒從未因任何毫無事實根據的神聖法令而獲得新生或被稱義。相反,信徒藉著聖靈與基督真正實現了本體論上的聯合,從而歸入基督的身體。若聖靈不曾建立上述聯合關係,則基督徒的義將淪爲「法律擬製」(legal fiction)。這一原則在兩個方向上適用:通過聖靈與基督聯合,以及通過肉身與亞當聯合。重要的是本體論上的關聯。如果全地的審判者行事公義,這兩項聯合都不能僅僅是法律上的假設。
暗示神可以立(亞當或基督爲)行政性的「元首」卻不提供本體論基礎還會導致另一個問題。我們再次以基督徒與基督的聯合爲例,這一聯合與」與亞當聯合「形成對照。想像一下,神通過神聖法令,白白使人稱義,但實際上,聖靈並未將基督徒與基督聯合起來。這種理論缺了什麼?聖靈。因此它不需要三位一體。如果保羅的」亞當——基督「類比成立,那麼智人可以在毫無真正聯繫的情況下與亞當聯合。這樣的推論會使我們採取次三一論(sub-Trinitarian)的救贖觀。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哥林多前書11:3的邏輯暗示,若夫妻間缺乏本體論聯繫,說丈夫是妻子的頭會很奇怪;而說父上帝作爲基督的頭,不需要任何父子間的本體論聯繫,則令人擔憂。將如此輕率的本體論觀點引入三一論,會使人陷入亞流主義(Arianism)或三神論(tritheism)。當然,暫時還沒有人試圖採取這一觀點,但我們有權質問,爲何不同情況下處理「元首「問題的方式差異如此巨大。
從聖經和神學方面看,如果物質現實中,亞當並非全人類的始祖,那他就不可能成爲全人類的「頭」。間接的經文證據似乎表明亞當是全人類的本源(徒17:26),除此之外,從神學角度,我們也不得不認爲,既然亞當被視爲全人類的「頭」,他也必須是全人類之父。
基督披戴我們的人性
早在納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將之清楚闡釋以前,使徒後的教會(post-apostolic church)很大程度上由如下思想塑造:在道成肉身中,基督並未承擔的受造物無法「治癒」或得救(見沙夫編著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英文438頁)。本質而言,這一思想試圖將希伯來書2:11-17的內容系統化。經文的內容爲:基督該與祂所要救拔的人相同,祂要照樣成爲血肉之體,使那些處在死亡詛咒下的血肉之體能夠死而復活,重獲新生。因此祂並不採取天使的形體——那與我們無關——而是成爲血肉之體,好讓祂自己與我們相同,從而真正救拔我們。異端破壞基督真實的人性,從而破壞基督的救恩,而正是前述的神學使教會免受這些異端的侵害。
如果亞當不是全人類的祖先,而只是智人多個互不相關分支中的一員,那麼格里高利的說法就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基督並非取了我的肉身,而是取了另一批人類的肉身,那麼祂就不是我的同胞兼救贖主。因爲如果使徒後的教會對希伯來書第2章的解讀正確,那麼重要的不是基督披戴了任何人性,而是祂披戴了「我們的」人性。
當神學教義脫離歷史的束縛,它們總是更容易與其他數據和意識形態互相協調。而且,許多教義顯然在本質上與歷史上的基督教並無直接聯繫。
我的論點是:亞當的身份,及其作爲人類肉身始祖的角色,並非隨意可丟棄的教義。亞當的歷史現實性作爲重要的手段,保證了基督教對於罪和惡的解釋以及對於上帝的理解,也維護了道成肉身、十字架與復活的基本原理。亞當是全人類肉身的始祖,這一點顯示了神在亞當中給我們定罪的公義(由此及彼,神在基督裡救贖我們的公義),也保護了道成肉身的邏輯鏈條。若有人別出心裁地解釋前述兩項信念,必然導致極爲嚴重的後果。
編注:本文摘自《基督徒應接受進化論嗎?——聖經與科學的回應》(Should Christians Embrace Evolution: Biblical & Scientific Responses)一書中作者撰寫的相關章節。
譯:Alice;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es It Really Matter Whether Adam Was the First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