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已經問世85年了,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這部著名小說今天依然被譽爲是爲我們這個時代量身定做的作品,這可能令人感到意外。作爲一部未來主義小說,在其想像的世界裡,它引發了許多關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探索的對話。
今年的週年紀念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由頭,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赫胥黎的經典大作,並思考它與當代世界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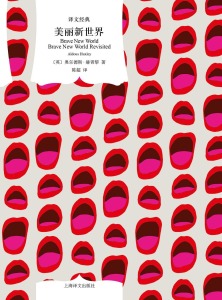 《美麗新世界》的敘事前提和批評對象來自赫胥黎的時代日益受歡迎的福特主義意識形態(Fordist ideology),小說將其投射到一個令人不安的烏托邦式的未來。在赫胥黎的「世界國」(World State)中,亨利·福特被推崇爲半神話式的彌賽亞式的人物。該書的紀年以他爲分野(書中的事件發生在632A.F. 意思是After Ford,即福特之後),他的名字——新世界的創始人——取代了上帝的名字。一次性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報廢勝過維修」),以及可預測和大一統的價值觀,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
《美麗新世界》的敘事前提和批評對象來自赫胥黎的時代日益受歡迎的福特主義意識形態(Fordist ideology),小說將其投射到一個令人不安的烏托邦式的未來。在赫胥黎的「世界國」(World State)中,亨利·福特被推崇爲半神話式的彌賽亞式的人物。該書的紀年以他爲分野(書中的事件發生在632A.F. 意思是After Ford,即福特之後),他的名字——新世界的創始人——取代了上帝的名字。一次性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報廢勝過維修」),以及可預測和大一統的價值觀,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
人類本身已經成爲「世界國」的超級福特主義的產品。透過一個龐大的優生學項目,人們藉著先進的生殖技術和條件得到大量生產,成爲社會中溫順、好用的參與者,然後完全投入到構成社會心臟的生產和消費之中。人類由五個不同的種姓或模式組成,每個都被精心設計和調教,以服務於特定的社會目的。社會強調同質性和一致性,個性化、家庭、一夫一妻、以及專一的愛情被視爲一種障礙而遭到抵制,「每個人都屬於其他人」。
統一的生產線塑造出孩子們,有性繁殖、一夫一妻以及父母的概念都遭到深惡痛絕。社會鼓勵公民們從事不育的濫交,以使他們對自己受奴役的狀態感到沾沾自喜,同時這也是一種防止人與人之間產生特殊依戀的手段。正如赫胥黎在導言中所說的,「隨著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減少,作爲補償,性自由往往會增加」。特立獨行和個人隱私都遭受質疑。
人口的巨嬰化是政府的既定政策。身體的衰老和性格與心智的成熟被阻斷,以使世界各國公民的能力和品味永遠處於青春期狀態。同質化的大眾娛樂文化促進了社會的凝聚力和穩定性。以「感官電影」("feelies")和流行的體育運動爲形式的強烈感官刺激,都鼓勵人們被他們衝動和慾望玩於股掌之中,不能延遲滿足,不能發展信念,不能深入感受,不能完全投入到任何一項事業之中。頭腦裡充滿感性和快感,最明顯的是通過接種神奇的致幻藥物「索麻」("Soma")來防止思考、杜絕反思和禁止不守規矩。
《美麗新世界》的標題是對莎士比亞《暴風雨》(The Tempest)中一句台詞的諷刺性引用。儘管表面上令人愉快,但「世界國」的技術官僚和快樂的社會抹殺了所有的激情、道德、意義、理想和莎士比亞筆下昇華的人物價值觀。輕鬆的性愛扼殺了浪漫;條件限制和藥物保障的「美德」代替了攻克己身和性格形成;無休止的舒適、快樂和缺乏鬥爭使高尚和英雄主義變得沒有必要。詩歌、犧牲、意義和上帝自己在這樣的世界中沒有地位。
閱讀《美麗新世界》可能是一種奇特的體驗,因爲人們會被古色古香的趣味和令人震驚的當下元素所一一震撼。儘管這部作品作爲一部未來小說已經過時了,但它仍然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儘管赫胥黎有先見之明和洞察力,但他的遠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所處的時代新興動力的投射和升級:即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和大眾社會。
這些動力已經被後來的許多發展所取代,或者至少是大大地複雜化了。在一個後福特主義經濟和個性化設備的數字時代,大眾社會不再像以前那樣簡單。例如,個性不但沒有被視爲一種威脅,而且現在已經深深地被我們的經濟體系所同化,因爲我們被鼓勵通過我們選擇的消費形式來區分、識別和調整自己。我們都戴著自己選定的鏈子,這讓我們都被捲入了同一個系統的事實不那麼凸顯。
事實上,從我們當代的角度來看,赫胥黎設想的一些元素似乎過於保守。在現代遺傳學出現之前,赫胥黎不可能輕易想像到我們現在可以對人類直接進行基因工程,以及由此獲得對人性的掌控力。他似乎也沒有預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性愛形式——《美麗新世界》中的濫交都發生在異性之間。此外,儘管赫胥黎構想了一個「世界國」,但爲赫胥黎的敘述提供背景的卻是英國:激進的全球化在這裡似乎效果有限。
赫胥黎描寫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細節是,雖然「世界國」建立在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上,但自動化的過程大大受到壓制,其實,人類從事的工作很容易轉交給機器或算法(赫胥黎沒有探討準智能機器的可能性)。從當代的角度來看,我十分懷疑小說中的這樣一個經濟體能夠被馴化以服務於更大的社會目的,哪怕是一個反烏托邦的目的。赫胥黎可能會擔心「世界的控制者們」把福特主義的意識形態炮製和強加在命令式的計劃經濟中,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崛起的時代,這種擔心並非捕風捉影;我們現在似乎更有理由擔心我們受制於一個失控資本主義系統的自主和貪婪的邏輯,這一切超出人類的設計或控制。
「世界國」是一個密集規劃的社會,可以直接以命題的形式呈現,並由統一的人類願景整合而成。《美麗新世界》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解說性的對話,明確闡述了支撐世界國家的人類意識形態。然而,最有力地塑造我們世界的社會發展似乎不再是通過計劃,也絕對不會直接呈現給我們。相反,這些社會發展更典型地表現爲我們啓動的技術和社會動力,其長期目標尚不清楚,其對我們的增量影響雖然總體上和回顧起來是巨大的,但只是在當下和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被間接地感知到。儘管我們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調節,但調節器更可能是一種技術,例如互聯網,而不是人類智能。
 在當今時代,我們更害怕我們啓動的無法控制和無情的非人道過程,這些過程在社會中以令人沮喪的必然性展現出來。我們的世界受制於資本主義總體化和技術進步的雙重力量。雖然後者擴大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範圍,但前者把消費、我們不受約束的能力以及衝動推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壓倒了一切可能限制它們的障礙。雖然人類是這些力量的走卒,但這些力量本身的驅動邏輯卻高過於人類。
在當今時代,我們更害怕我們啓動的無法控制和無情的非人道過程,這些過程在社會中以令人沮喪的必然性展現出來。我們的世界受制於資本主義總體化和技術進步的雙重力量。雖然後者擴大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範圍,但前者把消費、我們不受約束的能力以及衝動推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壓倒了一切可能限制它們的障礙。雖然人類是這些力量的走卒,但這些力量本身的驅動邏輯卻高過於人類。
這是《美麗新世界》願景產生共鳴的一個關鍵點。赫胥黎比大多數人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對享樂的渴求會使我們陷入一種有辱人格的束縛。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曾將赫胥黎的作品與奧威爾的《1984》進行過對比且非常出名,他觀察到,赫胥黎認識到,與恐懼相比,我們可能更容易被慾望所摧毀和支配。在快樂、娛樂、瑣事、分心、慾望和感官的麻醉下,我們可能會對我們的人性不斷被侵蝕而感到麻木。
在當代世界中,正如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觀察到的,我們受制於一種溫和的極權主義,它不斷地要求我們「享受!」。市場已經用產品和廣告把我們包圍,這些產品和廣告已經被當成武器,以激發和調動我們的消費慾望,並瓦解我們任何可能的抵抗。在這個過度飽和的超現實世界裡,我們接觸到大量人工創造的刺激,遠遠超過我們以前自然遇到的任何刺激:從化學工程食品,到電腦遊戲的炫目圖形,從改變心智的藥物,到我們屏幕上充滿活力的圖像,從在線色情內容,到精心剪裁的旅遊目的地,從雜誌封面上的氣質模特,到像臉書這類的網站上的社交。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爲了激發我們的飢餓感,克服我們的抵抗力,並促使我們放縱其中。資本主義令人陶醉的享樂浪潮壓倒了它面前所有的障礙——審查制度、法律限制、文化禁忌、社會規範、宗教美德、自我控制。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認爲,控制和約束食慾對人類自由至關重要,也是我們的基本權利之一。如果沒有這樣的控制,我們就會淪爲幼稚的快樂囚徒,無法自我管理。一個悲慘的例子是色情造成的巨大破壞,新技術增加了它的征服力,市場的力量使色情變得更有吸引力,也更難以對抗。雖然在赫胥黎時代,一個專注於大眾娛樂和體育運動的社會正在興起,但我們自己的社會對這些事物的癡迷程度——以及我們作爲基督徒對流行文化的相對毫無疑問的消費——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值得真正警惕。
赫胥黎進一步認識到人性被置於生產邏輯之下的危險。也許「世界國」最核心的現實是以技術生產取代了性生殖。人類不再以生育的方式繁衍而是開始被製造。赫胥黎敏銳地察覺到這一轉變是多麼關鍵,並提請我們注意其各方面的細節:純避孕的性行爲和相對的性別中立的文化,通過類似傳送帶的過程形成兒童,消滅家庭和自然地歡迎孩子進入的愛之紐帶,等等。
再一次,赫胥黎的這部作品中有一個方面在我們當代世界中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鳴。通過諸如墮胎的意識形態化、生殖技術的進步以及中性婚姻的正常化,孩子們越來越像是被選擇和建構的邏輯渲染出來的。人類尊嚴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不是被製造而是被生出來的——通過身體受孕,結成愛的禮物,這一切領先並超越人類在政治、法律、經濟和技術領域的所有活動。一種文化,如果抵制或忽視這一事實,就像我們現在傾向的那樣,可能會改變文化對於人類本身的理解和對待。
作爲21世紀的基督徒,我們正面臨著一場日益嚴峻且極其艱鉅的爭取人性和尊嚴的鬥爭。我們必須反對人類屈服於享樂的暴政,反對我們的文化將我們包裹在羊水般的感官享受之中,使我們對現實的感覺變得遲鈍,從而無法喚醒我們去承擔責任、去愛或去敬拜。我們必須抵制對我們本性進行技術控制的誘惑,這種控制會讓我們冒著被非人化的風險。爲了做到這些,我們必須認識並克服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背叛,它會從內部顛覆我們。面對這些加速的發展,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從未如此具有時代性,它所發出的警告也從未如此緊迫。
針對這些情況,我們必須重申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重申通過男女合一的愛來孕育新生命的重要性,重申劃定市場和技術發展的道德界限的重要性,以及重申上帝是生命的賜予者、我們都是由他創造的這一真理的重要性。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遭受有史以來最陰險捆綁的危險。
譯:PSJ;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Brave New World, 85 Years L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