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這是耶穌說過的話。但如果神所說的語言是我們難以覺察的,或者我們對祂的話油蒙了耳呢?
想像一下:我們不能明白神對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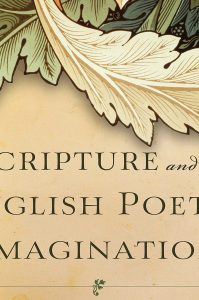 們說的話是件多麼可怕的事。可是耶穌警告祂的門徒,除非他們能解釋比喻——除非他們能詮釋比喻的講論——他們就聽不見神的啓示。貝勒大學文學人文學特聘教授大衛·萊爾·傑弗瑞(David Lyle Jeffrey),在他的《聖經與英語詩意想像》(Scripture and the English Poetic Imagination)一書中爲我們提供了一把明白神話語的鑰匙。傑弗瑞說,「耶穌已經暗示了他使用虛構、比喻、奧祕講論的目的既是爲了隱藏些什麼,又是爲了啓示些什麼,如此只有那些真心尋求其意義的人才會發現它。」要聽見神講話,我們必須將耳朵調準到詩歌頻道。
們說的話是件多麼可怕的事。可是耶穌警告祂的門徒,除非他們能解釋比喻——除非他們能詮釋比喻的講論——他們就聽不見神的啓示。貝勒大學文學人文學特聘教授大衛·萊爾·傑弗瑞(David Lyle Jeffrey),在他的《聖經與英語詩意想像》(Scripture and the English Poetic Imagination)一書中爲我們提供了一把明白神話語的鑰匙。傑弗瑞說,「耶穌已經暗示了他使用虛構、比喻、奧祕講論的目的既是爲了隱藏些什麼,又是爲了啓示些什麼,如此只有那些真心尋求其意義的人才會發現它。」要聽見神講話,我們必須將耳朵調準到詩歌頻道。
「神是位詩人」傑弗瑞提醒我們。「祂如何說話,而不單是祂說了什麼,是了解祂所是的重要方面。」 因爲沒有留意說話的形式,一個聆聽者可能會錯過信息的主體。就神的話語而言,傑弗瑞解釋道,「神經常像位詩人那樣說話」。打開聖經,看看傑弗瑞的宣稱是否正確吧:當你大聲朗讀聖經,有多經常聽到比喻?想想創世記中希伯來文的敘述模式,詩篇中的詩歌,還有那些顯而易見跳入你腦海的箴言、所羅門的雅歌,神對以賽亞和以西結詩歌體的預言,耶穌的比喻等等。考慮到詩歌在聖經中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說認識神部分上是基於我們對詩歌的閱讀理解能力。
傑弗瑞認識到大部分讀者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聆聽或享受詩歌。30多年前,著名的詩人達納·喬亞(Dana Gioia)問道,「詩歌有什麼用嗎(Can Poetry Matter)?」他注意到美國人有種傾向,認爲詩歌是無關緊要的。「儘管還是有人寫詩歌,」喬亞寫道,「它已經從文學生活的中心位置上退了下來。」閱讀詩歌就像陽春白雪的消遣,是住在東奧斯汀區帶著貝雷帽或穿著低腰褲的紐約人研究的東西。傑弗瑞發覺人們正傾向於認爲詩歌不是大眾所能染指的。
但是,詩歌的高雅正是我們應當閱讀它的理由。從傑弗瑞的觀點來看,詩歌的考究文學風格(elevated style)強化了內容的聖潔性。由此,詩歌可能要從日常講論中分別出來;它像是場與神祕的搏鬥,傾聽者抓住的是其實質的重量。「在神的國度中,爲了我們敬拜在上的神,」傑弗瑞建議,「我們需要詩性的藝術:讓我們能以獨特的方式接近聖潔;它是信心的僕人。」就像主日是從一週中分別爲聖安息的日子,好提醒我們永恆的本質,詩歌則讓我們重新看見詞句的重要和可畏,尤其是神的話。
《聖經與英語詩意想像》通過英語詩歌的歷史,爲我們描繪了方向。從喬叟到受聖經影響、以詩歌回應神的詩人安東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該書讓讀者一一重溫。它向我們展示了許多往日美好、不該失落的寶貝。因此,傑弗瑞的書也像一次翻拍,駛過文化的記憶,將傳統中我們離開的路徑向我們一一顯明,由此,我們知道該如何回轉。傑弗瑞說:
在我們對網絡的成癮耗盡了對美的感知力後,如果我們要過一個充滿想像力的未來生活,我們就需記得「以前的事是怎樣的」——那詩歌還未凋零,眾多廉價的小標題還未替代詩歌對心靈和頭腦提供豐富滋養的時代。
傑弗瑞花了後半本書的篇幅討論「宗教改革之後」以及在改教人文主義者中高舉「自身爲權威或道德例律的裁判者」的風氣。當然,這些是宗教改革「意想不到的結果」,但他們深刻地影響了浪漫與啓蒙運動時期作家的作品,其影響波及現代。如果我們閱讀早期英格蘭宗教改革時期詩人約翰·鄧恩(ohn Donne)和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作品,我們會體驗到忠心的基督徒作品,但詩歌本身卻轉向了個人自身。鄧恩寫作了懺悔詩、渴望救贖的詩歌,而赫伯特則寫下禱告詩,在自己的家中將這些詩歌讀給會眾聽並作爲牧養的手段。但丁或喬叟時代的詩歌——與神學、政治緊密連結,將教會視爲學院——已經漸漸被以內省爲主要目的的詩歌所替代。
傑弗瑞沒有花篇幅在異端邪說的浪漫派詩歌上(我的淺見,不一定是他的想法),直接從17世紀跳到了繼承錯誤異象、以自我爲參照的現代詩歌上。他引用了1953-1954年約翰·麥克莫瑞(John MacMurray)在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上的警告:
首先,現代哲學將自我作爲它的起點……其次自我是一個孤立的個體……自我的前提是個尋找知識的思想者,也就是尋找那些有幫助信息的人。
帶著這樣關於自我的預設,還會有什麼人讀詩歌呢?更糟糕的是,認爲個體帶著孤立的本性,以此爲假設的詩人不可避免地寫出晦澀,無意義的詩歌來。傑弗瑞認爲現代主義的座右銘簡而言之就是:「對你而言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你自己。」
這或許能解釋爲何詩歌從潮流中落伍。就像傑弗瑞所說,「現代詩人感覺自己必須在任何公眾視野之外。」如果我們是疏離的意義製造者,我們就對讀者沒有任何責任,對任何在上或名譽之外的事沒有熱情,對任何道德判斷沒有權威。傑弗瑞哀嘆道,「現代詩人的一個困境就是他們的聽眾知道的詞彙越來越少。這進一步切斷了與過去的對話。」
但是在現代詩人中間,在當代英語詩歌中仍有盼望。那些尋找表達「個人性作爲一種關係」的詩歌,那些激發「不單是私人體驗也是共同回憶」的詩歌,將帶我們回到「某些共同的異象中。這樣的詩歌將成爲我們回家的路。」
在《圖像:宗教與藝術日誌》(Image: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the Arts)中,凱瑟琳·威利斯·佩施(Katherine Willis Pershey)論到,「在這個充斥著戰爭罪惡和汽車廣告的世界中,詩歌悄然而堅定地吸引著我們去注視那些尋常的美好與終極緊要的事。」
詩歌爲不可言喻的奧祕命名。當尋常的詞語讓人覺得像是沉悶、過熱的引擎發出的哼鳴之音時,詩歌就像神的介入一般,打破了一切,以至於我們可以再次聽見神是誰,我們是誰。沒有詩歌的話,我們也許注定將像電腦代碼那樣交談,像毫無意義的廣告標語,或者像吼叫的動物一般。詩歌在受造的次序中,提升我們來到富有創造性的受造者地位上。
如果就像傑弗瑞提醒我們的那樣,神是「詩人的鼻祖——是寫出了世界的那位,」那我們就必須學習傾聽詩歌。否則我們就成爲耶穌所警告的那群,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的人。
譯:EYZ;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Christians Need a Poetic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