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拿單·愛德華茲對自然世界著迷。他從小就經常分析他周圍的世界,認爲 「自然與普遍性護理之書」顯明了他所敬拜這位造物主的諸多屬性(《約拿單·愛德華茲作品集》,第11卷,50頁)。愛德華茲對聖經中的預表和「神聖事物的影子」的關注是這位北安普頓牧師的持久遺產的一部分(51頁)。因此,在70多年前,學者們就開始對其作品進行註釋和編輯。設在耶魯大學的約拿單·愛德華茲中心最終出版了26冊紙質書,然後將注意力轉向電子版本的製作。
除了這些學術上的努力,諸如「真理旌旗」(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和「渴慕神」(Desiring God)這些跨教會機構也致力於在教會中推動閱讀愛德華茲的著作。他們共同爲仰慕這位可以說是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哲學家的新一代鋪路。這些「年輕、躁動的改革宗」福音派基督徒發現,愛德華茲絕不僅僅是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他是一個英雄。
英雄的問題是,他們的斗篷會起皺。簡而言之,他們會讓我們失望。我們就必須了解他們的不足並決定如何應對。
愛德華茲也不例外。事實上,他的某些失敗會變得格外顯著,這在人們試圖使用帶著註釋和批判性文字的版本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生活和思想時尤爲凸顯。也許愛德華茲所犯的錯誤中最有問題的是他對基於種族的奴隸制有著全面性的參與。不管如何爲他辯護,愛德華茲這個奴隸主離我們希望的英雄頗有距離。然而,歷史上的愛德華茲不僅促使我們拒絕把他僅僅當作精神遺產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且讓其他一些頗具影響力的美國思想家,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溫德爾·貝瑞(Wendell Berry),幫助我們認識到歷史的力量,以促進有意義的反思和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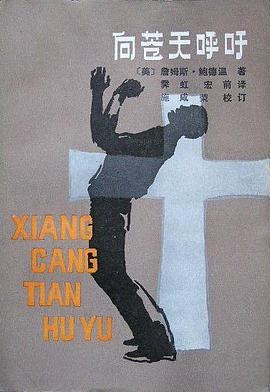 詹姆斯·鮑德溫以半自傳體著作《向蒼天呼籲》(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臺譯《山巔宏音》)登上文壇,該書聚焦於哈萊姆居民約翰·格萊姆斯的生活以及他與家庭、教會和信仰的脆弱關係。在此後的十多年裡,他繼續在《烏木》特刊中處理歷史研究的問題。在《白人的罪疚》(「The White Man’s Guilt」)一文中,鮑德溫談到了歷史研究的實踐,不僅對這一學科的前景作出意義深遠的解釋和反思,而且說明了將其簡化爲重述遺產和簡化版英雄故事的危險性。作爲一名美國的種族史學家,我發現鮑德溫對歷史學科的危險和作用的論述極具指導性和挑戰性。
詹姆斯·鮑德溫以半自傳體著作《向蒼天呼籲》(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臺譯《山巔宏音》)登上文壇,該書聚焦於哈萊姆居民約翰·格萊姆斯的生活以及他與家庭、教會和信仰的脆弱關係。在此後的十多年裡,他繼續在《烏木》特刊中處理歷史研究的問題。在《白人的罪疚》(「The White Man’s Guilt」)一文中,鮑德溫談到了歷史研究的實踐,不僅對這一學科的前景作出意義深遠的解釋和反思,而且說明了將其簡化爲重述遺產和簡化版英雄故事的危險性。作爲一名美國的種族史學家,我發現鮑德溫對歷史學科的危險和作用的論述極具指導性和挑戰性。
鮑德溫沒有說一些歷史總是在重複之類的廢話,他敏銳的分析令人信服:
幾乎沒有人知道,歷史不僅僅是用來讀的。而且,它不僅僅指向過去,甚至也不是在原則上指向過去。相反,歷史的巨大力量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帶著它,在許多方面無意識地受它控制,而歷史也確實存在於我們所做的一切之中。(《烏木》特刊,47頁)
如此看來,歷史對所有人爲自由和公義所做的掙扎都大有裨益。歷史幫助我們確定自由和公義是什麼、不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鮑德溫斷言,「正是由於歷史,我們才有了我們的參考框架、我們的身份和願望」。(47頁)歷史不僅僅被當作「過去」對待,它也在不斷塑造我們現在和未來的生活,需要將其與遺產分開。
雖然並不總那麼明確,但與「歷史遺產」相關的呼聲在最近幾個月和幾年中重新響起。當美國白人抗議真正的歷史遭到抹殺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時候並沒有真正指向歷史。相反,他們是在用「歷史遺產」的概念來代替,而這種「遺產」只不過是一種扭曲的歷史感而已。如果你願意,這就是一個被替換的現實。與鮑德溫談論的歷史不同,遺產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存在。遺產可以在方便的時候與我們的行動分開。有意將遺產誤標爲歷史近來似乎很常見。這種混淆使我感到憂愁。
我的悲傷源於我們願意在這種虛假之上發展,條件允許的時候我們就能從中獲利,即或不然我們就躲起來。然後,即使我們「朦朧地或生動地意識到(我們)餵給自己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個謊言」,正如鮑德溫所感嘆的那樣,但我們不僅堅持,而且還致力於爲其開脫,因爲我們在整個社會共同認知的故事中出局了。鮑德溫預言道(47-48頁):
這種「出局」的性質可以簡化爲一種懇求:不要怪我,我不在那裡。我沒有做過。我的歷史與歐洲或奴隸貿易毫無關係。無論如何,是你的酋長把你賣給了我。我沒有經手,我不對曼徹斯特的紡織廠或者密西西比的棉田負責。此外,想想英國人在那些紡織廠和那些可怕的城市裡是如何受苦的!我也鄙視那些總督。我也鄙視南方各州的州長和南方各縣的警長,我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受到體面的教育,並在他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升到最高。我沒有針對你,沒有!我沒有針對你。爲什麼你還要對我不滿呢?你想要什麼?
有了這種維護遺產——而不是歷史——的糟糕努力,我們很容易發出信號,爲自己、我們的遺產和英雄辯護。
了解了鮑德溫對歷史和遺產之間區別的解讀,我們可以回到愛德華茲。我們常常傾向於捍衛我們的遺產和英雄,甚至超過捍衛我們自己。這幾乎就像在相信除非我們奉承他們,否則他們就無法生存。相反,我們這樣做最終會摧毀這些英雄和我們自稱熱愛的過去。
一種比較大眾化的扁平化某些歷史人物的方式就是把他們抽象化。我們何時以及如何做到這一點呢?當我們被迫去面對他們生活中那些不那麼令人滿意的部分時,常常會把英雄們抽象化。正如溫德爾·貝瑞提醒我們的那樣,「無論在哪裡,抽象都是敵人。」當我們把一個英雄描述爲「他時代的人(注意,幾乎總是一個人)」時,貝瑞的說法再真實不過了。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就像一個敵人,使人和歷史都被扁平化。
我們把英雄扁平化的另一種方式是有意識地忽視或有時忽略他們的失敗,因爲我們所謂的未知拒絕處理我們已知的東西。二十年來,我一直在分析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和種族構建的交集。我試圖把重點放在我們可以知曉的那段時間和那個地方的一些主要人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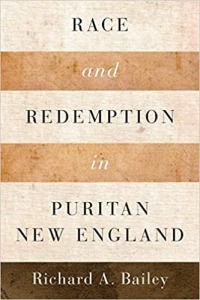 從一開始,沒有人比愛德華茲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出現在我的《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種族與救贖》(Race and Redemption in Puritan New England)的每一章中。由於我無法在這裡充分探討所有這些內容,我將利用這個機會鼓勵你更全面地探討我的書。不過,我確實想指出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愛德華茲的幾個事實,以及他在北安普頓國王大道的房子裡參與奴役其他人類的做法和以種族主義的姿態對待他的黑人和原住民鄰居這一過程。
從一開始,沒有人比愛德華茲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出現在我的《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種族與救贖》(Race and Redemption in Puritan New England)的每一章中。由於我無法在這裡充分探討所有這些內容,我將利用這個機會鼓勵你更全面地探討我的書。不過,我確實想指出我們所知道的關於愛德華茲的幾個事實,以及他在北安普頓國王大道的房子裡參與奴役其他人類的做法和以種族主義的姿態對待他的黑人和原住民鄰居這一過程。
首先,約拿單·愛德華茲一直把非洲男人、婦女和兒童視爲個人「財產」。這種想法可以從他爲自己和他人購買人口和租借奴隸中看出。例如,在1731年訂立的一份賣身契中,這位年輕的牧師買下了一個名叫維納斯的年輕女孩——他認爲是屬於個人財產的至少七個人中的第一個。在這一常規法律交易之後,他又採用了另一種奴隸主慣常的做法,就是將維納斯改名爲利亞。這樣一來,這個14歲的女孩立馬就從希臘的愛神變成了聖經中不被愛的妻子——再次將她的身份定爲低人一等。
關於奴隸主愛德華茲的另一個事實是,他(和他的父親提摩太·愛德華茲一樣)參與了租借奴隸的貿易。將人租借給社區裡的其他人可確保奴隸主的投資得到回報。正如愛德華茲的妻子撒拉寫給鎮上警察的一封信中所寫的那樣,愛德華茲確實把利亞租了出去,可能是爲了補貼他經常被拖欠的工資。利亞被租借出去也表明,愛德華茲與大多數新英格蘭人一樣,將受奴役的婦女視爲家庭的一部分。在她給警官的信中,撒拉請他轉達她和她的孩子們"對利亞的愛"。這樣的感情表達說明了有關愛德華茲參與奴隸貿易的另一個事實。他和他的家人與奴隸建立了情感上的紐帶,即便與此同時他以一種種族主義的姿態對待他們。
儘管爲利亞創造了這樣一個身份,這個以前被稱爲維納斯的年輕女孩還是在1736年加入了北安普頓教會。因此,我們得知有關愛德華茲種族思想的另一方面是:他歡迎新英格蘭的有色人種進入當地的屬靈共同體。他接納黑人歸信者成爲正式的教會成員。在後來被稱爲「第一次大覺醒」的復興時期,這種身份對有色人種來說更加普遍,其中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可以參與當地教會的生活。例如,愛德華茲在給人施洗前的教導記錄包括他對黑人初信徒提出的具體問題。
黑人教會成員也可以在對白人執行教會紀律的時候出面指證那位白人成員。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提到於1744年發生在年輕人中間的聖經爭論中出現了這樣的證詞。在發現一些年輕的白人男子利用助產手冊騷擾社區婦女後,塞斯·波默羅伊少校的非洲奴隸巴斯希巴作證,指控提摩太·羅特和他的同謀者(馬斯登,292頁)。因此,一個黑人的聲音幫助了會眾對犯罪者悔改的呼籲。
我們還知道,愛德華茲爲其他奴隸主辯護,並含蓄地爲自己辯護。在1740年代初,他替一位陷入爭議的「舊光派」牧師本傑明·杜利特爾(Benjamin Doolittle)起草了一封信。馬薩諸塞州諾斯菲爾德的會眾試圖(第三次)罷免杜利特爾,他們聲稱,他不適合做他們的道德和屬靈領袖。指控是什麼?杜利特爾是個奴隸主。愛德華茲應要求爲杜利特爾和奴隸制辯護。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明確表示,雖然他支持奴隸制,並從奴隸制中受益(就像大多數新英格蘭白人直接或間接地受益一樣),但他認爲海外奴隸貿易及其綁架人的做法在道德上是令人厭惡的。在爲這一自己不喜歡的神學立場辯護的時候(他最終給被奴役的阿比雅·普林斯發了工資),他也說明了對基於種族的奴隸制中某些因素感到不快。
在他買下維納斯後不久寫的一篇私人文章中,愛德華茲明確表示,他對奴隸主經常虐待被他們視爲私有財產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感到不安。他的「空白聖經」中一個條目暗示了他在如何對待這些人方面的掙扎。最初,愛德華茲寫道,約伯記31:13-14「清楚地說明了我不應該輕視和虐待他人的原因」。愛德華茲也許是對他的解經過於個人化而感到不舒服,就再編輯了他的註釋,解釋「爲什麼約伯不應該輕視和虐待他的僕人」。這位永遠謹慎細緻的遣詞造句者的修改表明他有時會對作爲奴隸主所帶來的問題感到掙扎。
愛德華茲在這方面並不是特例。例如,他的表弟(有時也是巡迴佈道的夥伴)司提反·威廉姆斯也記錄了他自己在對待奴隸方面的掙扎。威廉斯在擔任馬薩諸塞州朗米多的牧師時,寫了60多年的日記。在日記中,他經常記下自己身爲奴隸主的做法,包括幾個具體的地方提到他在精神和身體上虐待非洲男性奴隸,至少有兩個人被逼自殺。
約拿單·愛德華茲也有類似的行爲嗎?有可能。不過,我們從他的「空白聖經」手稿中得知他可能與奴隸發生過肢體衝突,這些互動可能使愛德華茲本人也受了傷,溫德爾·貝瑞將其描述爲隱藏的傷口。
我們不必把愛德華茲抽象地看爲「他那個時代的人」,或爲我們不知道的事情辯護。相反,我們應該在他明顯犯錯的時候對他進行批評。他一生參與基於種族的奴隸制顯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即使是無意的,愛德華茲也促成了我們國家和教會中的一些種族主義的基礎:一個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經濟穩定的國家,以及由雖然共同敬拜但彼此根本不平等的成員組成的教會。當他所說的神學和教義是正確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保持向他學習的意願。
這樣的堅持希望能說明,我不認爲我們應該停止閱讀愛德華茲或研究他的生平和作品。話雖如此,但經過二十年來了解愛德華茲的一些想法和行動如何導致災難、種族主義、虐待和奴隸的死亡,我理解並尊重選擇不同方法的人。儘管如此,我不認爲這樣的路線對約拿單·愛德華茲(和許多其他歷史人物)是最好的。相反,我認爲我們可以、也應該向他學習。不過,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願意承認他做錯的地方,並明確地予以譴責。
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要學習愛德華茲的榜樣。當他認爲他的英雄們犯錯時,他就會說出來。即使這個英雄是他通常被稱爲「馬薩諸塞州西部的教皇」的外祖父和導師所羅門·斯托達德。即使這種立場最終以他在1750年被北安普頓的教會開除而告終。在這樣的時刻,愛德華茲預見到了詹姆斯·鮑德溫的想法,並建議如何對待歷史及其不完美的演員。但是,即使他在與教會有關的重要問題上與斯托達德意見相左,愛德華茲也沒有試圖推翻他導師一切的教導,因爲他相信上帝的工作比斯托達德更重要。他在1739年透露了這樣的想法,當時他講了一系列以歷史爲主題的30次佈道,一再指出他所敬拜的上帝是如何利用不完美的男女信徒來完成超越自己的工作。在他看來,這些人並不是故事中的英雄。相反,愛德華茲認爲,唯一的英雄是救贖人們的上帝。
約拿單·愛德華茲過著一種信心的生活。雖是不完美的生活,但還是一種信心的生活。而且,正如斯科特·哈夫曼所言,信心的生活教導人們很多有關賜下應許的神的功課。或者,引用1739年在愛德華茲死後出版的《救贖大工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系列中的概念,對歷史的研究中揭示了許多關於救贖的內容。愛德華茲在分析過去,向他們指出改變未來的可能性時,並不關心如何奉承在北安普頓的會眾或他的前輩。他很可能贊同鮑德溫的說法,即「那些想像著被歷史恭維的人(確實如此,因爲他們寫了歷史),就像針上的蝴蝶一樣被釘在歷史上,無法看清或改變自己和世界」(《烏木》特刊,47頁)。因著對聖經中的預表感興趣,愛德華茲可能會把被刺穿的蝴蝶解釋爲他所敬拜的上帝通過十字架的工作救贖選民的影子,他認爲通過拔掉針,歷史的上帝在世界中實現了真正有意義的改變。
重要的是,我們不僅僅要把約拿單·愛德華茲看作是一個英雄。他生活在歷史中。有時他成功地做到了馬太福音22:34-40中上帝的律法。在其他時候,他卻失敗了。他在種族和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無疑沒有踐行愛上帝和愛鄰舍的誡命。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失敗中學習。
認識到正面且具體的歷史力量,並拒絕接受令人愉悅的遺產替代現實和抽象的英雄,這不僅使我們做好準備處理過去和我們所知道的事情,而且做好準備面對現在和未來。面對種族偏見和白人至上主義,這種研究種族具體歷史問題的方法不僅使我們能夠處理種族主義對個人和系統造成的真正創傷,而且還能夠促進實際的變革和種族正義。
譯:SJH;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Should I Still Read Jonathan Ed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