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就像C. S.路易斯(C. S. Lewis)所建議的那樣,我們要幫助我們的讀者「讓這幾個世紀以來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心」(出自On the Incarnation: Saint Athanasius with an introduction——譯註)。也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只有通過閱讀經典」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接下來要審視一些可能被遺忘、但是依然和現今的教會相關,並且能幫助今日基督徒的經典著作。
作爲一個美國基督徒,我非常清楚明白自己正身處一個走向世俗化的國家。當說到世俗化的時候,我並不是指大多數美國人都是無神論者或是不可知論者; 也不是說大多數美國人不願意將他們的信仰帶入到公開的討論中。相反,我的意思正如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那樣:在這個世界上,基督教已經不再是每個人的默認立場,基督信仰需要與許多的宗教和意識形態激烈競爭、此消彼長。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在社會和政治的問題上人們缺乏合一,爭論越發增多。此外,歷史性的和合乎聖經的基督教越來越被看做是難以置信、不可想像,甚至是應當受譴責的。凡不拋棄這些傳統信條的基督徒們會被認爲或是愚昧,或是邪惡,或兩者皆是。這伴隨著基督教從公共場所被塗抹掉的重大社會變革,是有其歷史根源的,並且很少有人能夠像19世紀荷蘭歷史學家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 1801-1876)那樣,去幫助我認識我們現在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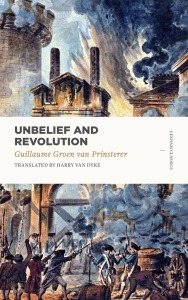 在本文中,我會著重介紹葛瑞恩被人遺忘的經典著作:《不信與革命》(Unbelief and Revolution),最近萊克斯漢姆出版社(Lexham Press, 2018)出版了新的英文版本。葛瑞恩曾擔任過荷蘭聯合王國威廉一世國王的內閣祕書長,之後成爲檔案館長、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報刊發行人和編輯。此書根據他在許多星期六的晚上在自己家中向一群朋友或熟人開設的講座整編和刪減而來。
在本文中,我會著重介紹葛瑞恩被人遺忘的經典著作:《不信與革命》(Unbelief and Revolution),最近萊克斯漢姆出版社(Lexham Press, 2018)出版了新的英文版本。葛瑞恩曾擔任過荷蘭聯合王國威廉一世國王的內閣祕書長,之後成爲檔案館長、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報刊發行人和編輯。此書根據他在許多星期六的晚上在自己家中向一群朋友或熟人開設的講座整編和刪減而來。
葛瑞恩的這些講話發表於1840年代,那段時間正值政治混亂席捲歐洲。他特別擔憂革命思想從法國大革命滲透到荷蘭社會中,也擔憂神學貧乏的荷蘭教會採用了理性主義或神祕主義的解經法,並忽略或拒絕古舊的教義和信條。
葛瑞恩的觀點是法國大革命不應當被視爲是一場過去年代的失敗政治項目。相反,葛瑞恩申辯道,這場大革命通過它危險的思想仍舊活著,會持續造成西方在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層面上的震盪,並周而復始地上演革命。大革命的精神將人取代神,將個人自我理性取代神聖啓示、將普遍的自我認定的道德取代了超越性道德。
考慮到大革命將神、啓示和超越性的道德排擠到一邊,它期望以社會一致爲基礎來確立道德和社會的秩序,並以當權者的意見爲基礎來決定「正義」的概念。爲了回應,《不信與革命》呼籲恢復:歐洲社會應當回到這個認知裡——道德律的設定和創造秩序有關,政治權力是由神命定的,法律和正義是根植於一個由神設立的客觀道德律,以及真理是客觀的並根植在上帝對他自己的啓示裡。
葛瑞恩辯論到,若歐洲社會不回歸到他們的基督教根基, 他們必將經歷由他們不信而帶來的後果。那些革命原則揉合形成一種有關人性、邪惡、救恩和末世的觀點,和基督教信念背道而馳。它們甚至是和創造的最基本秩序是對立的,而這樣做必然帶來嚴重後果。
這本書的前兩章是導論 。葛瑞恩決定寫下這一系列講座是因爲作爲一位歷史學家的他深刻意識到荷蘭的國恥和衰落(第1頁)背後的原因。在他的研究中,他總結了大革命關於自由、平等、人民主權論、社會契約論並社會重建這些思想,都是和基督教並創造秩序相悖的。「福音和實用主義無神論正在進行著生死較量,想要在這兩者之間達成友好關係,這是不可能的。」(第4頁)因此,基督徒就有義務在政治上去抵制這些大革命思想。
。葛瑞恩決定寫下這一系列講座是因爲作爲一位歷史學家的他深刻意識到荷蘭的國恥和衰落(第1頁)背後的原因。在他的研究中,他總結了大革命關於自由、平等、人民主權論、社會契約論並社會重建這些思想,都是和基督教並創造秩序相悖的。「福音和實用主義無神論正在進行著生死較量,想要在這兩者之間達成友好關係,這是不可能的。」(第4頁)因此,基督徒就有義務在政治上去抵制這些大革命思想。
葛瑞恩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對大革命的原因是基於自己歷史性的、合乎聖經的基督教立場。「聖經包含了司法和道德的基礎,也包含了個人自由和國家,政府的自主和權柄的基礎。經過真誠審慎地思索,聖經,是絕對無誤可靠的基石。」(第11頁)儘管感恩於有許許多多有智慧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葛瑞恩卻是「首先尋求聖經」。(第18頁)
在第二、第三、第四章中,葛瑞恩指出了那些雖推動了大革命的發生,但並不是造成革命的最主要因素。他爭論道,大革命的爆發並非因爲法國的現行原則和既定的政府形式的缺陷,或是法國政權的真正權利濫用。相反,它是那毫無廉恥的法國哲學家們有意爲之的計劃,目的是要敗壞和瓦解基督教的歷史,並它對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影響。按著這一方向,我們繼續讀到……
葛瑞恩開始探討大革命的根源——並隨之而來的不公義和暴力——是社會契約論代替了歐洲原普遍認爲政府乃由神所設立的歷史觀點。他批判洛克(Locke)和盧梭(Rousseau),尤其反駁霍布斯(Hobbes)。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用他的自然法思想主張掌權者擁有絕對的,接近神的權利,以來拯救人類免遭自身的殘酷暴行。諷刺的是,如畜類一樣嗜血的大革命卻揭示了它的面目:不是人類的救世主,而是他們的儈子手。
接下來,葛瑞恩開始針對一些評論家們的指控,即宗教改革帶來的與羅馬天主教的決裂助長了大革命。葛瑞恩反對這一觀點,並駁斥道:宗教改革對自由的強調是構架在其他的教義之上的,例如神的主權和人的墮落。宗教改革幫助減緩由歐洲滑向不信帶來的敗壞和衰退。
他說,宗教改革的能力不是在於科學定律或哲學性的辯護,而是在於傳講福音和基督教的基要真理(第82頁):
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不可磨滅地烙印在教會歷史上。我想到是聖經的無誤、救主的神性、聖靈的位格、我們本性的全然墮落,對我們罪責要付的代價、基督之義的歸算、重生和成聖的必要性——所有這些都概括成一件必要的事:平安惟有透過十字架上的寶血。這些真理都不變地出現在所有福音派教會的標誌性著作裡……這些真理和大革命所否認的真理是一樣的,而否認這些真理就是造成大革命的因素和根源的記號。
這些真理一旦被否認,那大革命就在所難免的。確實,不信的原則和由它邏輯所帶來的後果,必然引致毀滅。一旦歐洲與福音變得毫不相干,「沒有人(可以)阻止衝向深淵」。(第82頁)
在他的第八章中,葛瑞恩強調了在宗教界範圍內的不信。在歐洲的社會——包括了絕大部分的教會——不斷地拒絕符合聖經的基督教,由此不信的大革命意識形態便填補了這空缺,並且反而是大革命的意識形態給自己披上了基督教的觀點,比如公義、自由、包容、人性和道德。
但這些觀點其實並不是在大革命的土壤上孕育而出,而是在基督教的土壤裡。一旦正統不能保存這豐富的傳統,它就落入了哲學家的手中。那他們會用它做什麼呢?全都用來爲他們自己誇口,這些珍寶在他們的管理之下必要走向敗壞。這沒什麼好驚訝的。他們一面想要保留結論,一面卻摒棄前提,想要水卻同時又塞住水源,砍掉了樹根又想享受樹蔭。那些在福音溪水邊繁茂的樹木,當被移植到一個乾旱之地,下場只有枯乾。(第87頁)
對葛瑞恩來說,神是信仰和社會的源頭;當我們在對神的認知上出了錯,我們也將必然在生命的各個方面都會出錯。不信必然導致暴政。「無論謊言在哪裡勝利,它必然厭惡任何真理存留的元素」。(第93頁)那大革命的定義性特徵,就是恨惡神和福音——所以它就帶著「地獄的標誌」。 (第94頁)
 在第九章中,葛瑞恩展示了因爲在信仰方面的錯誤導致了在政治和政治學說方面的錯誤。然而從歷史上來說,西方世界一直都普遍接受神的主權是國家和社會的根本,現在它則宣告人的自主才是根本。從認知論來說,自主篡奪了神啓示的地位,真理變成了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事。從倫理上來說,司法逐漸等同於權宜之計。
在第九章中,葛瑞恩展示了因爲在信仰方面的錯誤導致了在政治和政治學說方面的錯誤。然而從歷史上來說,西方世界一直都普遍接受神的主權是國家和社會的根本,現在它則宣告人的自主才是根本。從認知論來說,自主篡奪了神啓示的地位,真理變成了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事。從倫理上來說,司法逐漸等同於權宜之計。
不信的政治學說中心是錯誤的人類學,它將罪的根源歸咎於制度而非人自己。大革命的政治學說假設人類的本性是好的,但是被制度給扭曲了——所以我們必須改善制度,或許由此可以再一次變好。特別是,我們必須廢除一切形式的階級制度,將社會想像成是每一個個體的集合體,並摒棄一切的差異、不同和不平等。
再進一步,國家該取代神,而不是被看做是神所設立的,要求所有公民都該將自己的生命獻於國家。結果就是,信仰必須服從於國家:
革命的國家針對信仰會有怎樣的政策呢?就是包容所有的信仰而它自身卻沒有信仰。當然得有一個附加條件,就是國家必須控制所有對它自身政治和道德的規則的敬畏,並禁止任何拒絕向這偶像下拜的信仰。(第103頁)
葛瑞恩總結到,不信的原則雖然保證自由,但最終的結果是,在撕裂的社會結構中或是在政府的極權統治之下,產生的要麼是激進主義,要麼是獨裁主義。(第107頁)
在第十章中,葛瑞恩提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不可能因無視創造秩序而沒有任何後果。歷史上充斥著異教徒的意識形態如何遭遇對抗神聖秩序的例子。大革命的思想也不例外; 它們積極地並重復地與創造秩序和神聖律法爭競。(第109頁)隨著革命派推翻了基督教各方面和道德秩序,他們接下來將單單追求感官的愉悅和屬世利益。
但是感官的愉悅和屬世利益這些偶像將會帶來負面的結果,這些結果會變得日益嚴重、社會結構將會分裂、國家將會被召喚來改善這結果。事實上,葛瑞恩在第十一到十四章中,清晰表明一個五個階段的週期,革命都會經歷它們不信的意識形態帶來的負面結果。
在他的結尾,葛瑞恩鼓勵基督徒們去傳講福音,呼籲他們去思想即使大革命的觀念非常有影響力,但是福音卻更加有力。我們必須傳講福音——儘管沒有回應甚至可能是逼迫。葛瑞恩寫道(247-248頁):
信心必然勝過世界。若我們想要勝過世界,那它必然首先是要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要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讓我們常記得那呼喊:「求主幫助我的不信!」 是在喜樂歡呼之前; 「主啊,我信!」讓我們永不忘記所有的行爲,包括在歷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在鑑察人心的上帝面前都毫無價值,除非藉由雙重禱告,就是表達了哲學家的共同需求和孩子般的呼求:「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以及「我的性命幾乎歸於塵土,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我特別慶幸當我十年前在瀏覽一個舊書店的書架時,找到了葛瑞恩的《不信和革命》這本書。儘管我找的那版本在金錢層面來說幾乎毫無價值——褪色破爛——但它有能力幫助我們去明白西方世界反覆發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動亂,這是無價的。儘管我並不是全部認同他呼籲的所有事情——例如,我並不贊同君主制共和國——但是我當時就覺得他所說的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不信根源是對的。
僞裝中立的西方革命意識形態如同救恩體系般運作,正是因爲如此,西方不斷繼續經歷社會和政治的動亂。創造秩序和道德律不可能矛盾而沒有後果。還有,正如葛瑞恩正確預測那樣,這種處境只會變得更加糟糕,除非神賜予我們屬靈的更新和文化及政治上的歸正。
譯:Lemon;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an Obscure Dutch Historian Helped Me Understand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