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J. D. 萬斯的這本《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出現在紐約時報夏天暢銷書榜單上的時候,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之所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因爲我以爲這肯定是「那種書」,那種進一步強化對阿巴拉契亞地區美國人刻板印象的書,在那些書裡——借用作者的語言——當地人就好像沒有牙齒、近親繁殖的白癡一樣。
像一個典型的鄉下人一樣,我對那些把我的家鄉當作無知、種族主義、無可救藥地陷在上世紀扭曲時光中的外鄉人很警惕。我在佐治亞州東北部的丘陵和凹地("hollers")長大,在一個小鎮上,上帝和國家——無論積極還是消極地理解這兩個詞——都是社會-政治上保守主義的同義詞。
我的親戚們都是在建築工地和農場工作的樸實人。他們在雜貨店裡宰肉、在大風暴後修理電線,也在當地學校教書,照顧著擁有昂貴住宅的「外來人」家門口的草坪。他們聽著喬治·瓊斯(George Jones)的歌,去沃爾瑪購物。
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獲得通過後,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我家的生意也在2008年經濟大衰退中受到重創。我的族人和萬斯的族人一樣,都是「紅脖子」、藍領工人、白人中產階級——這群人是美國重要的宗教和投票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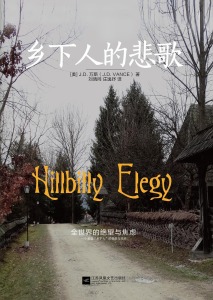 但是打開書後才翻了不到兩頁,作者就打消了我對刻板印象的顧慮。萬斯的悲歌(也就是一首哀歌)透過他作爲一個阿巴拉契亞人的經歷來審視我們這個嚴重分裂的國家。「美國有一個問題,」他寫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講述當你出生時脖子上就掛著一個問題會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當萬斯娓娓道來他艱辛的個人敘事時,我聽得津津有味:從肯塔基州東南部山區的生活,到俄亥俄州米德爾鎮的鐵鏽帶,他的家人搬到那裡是爲了從事某個行業,這行業最終離開了小鎮,留下了失業和痛苦。
但是打開書後才翻了不到兩頁,作者就打消了我對刻板印象的顧慮。萬斯的悲歌(也就是一首哀歌)透過他作爲一個阿巴拉契亞人的經歷來審視我們這個嚴重分裂的國家。「美國有一個問題,」他寫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講述當你出生時脖子上就掛著一個問題會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當萬斯娓娓道來他艱辛的個人敘事時,我聽得津津有味:從肯塔基州東南部山區的生活,到俄亥俄州米德爾鎮的鐵鏽帶,他的家人搬到那裡是爲了從事某個行業,這行業最終離開了小鎮,留下了失業和痛苦。
像許多來自山區的破碎家庭一樣,萬斯主要是由他的阿公阿嬤撫養長大的。他和生父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小時候在阿公阿嬤的家中和母親以及母親各種來回切換的同居男友/短期丈夫組成的家中長大。
阿嬤是這本書中的核心人物。和她那一代的許多祖父母輩一樣,阿嬤是維繫這個家庭的粘合劑。我很了解阿嬤,因爲我家裡就有一兩個這樣的老婦人。我也很了解阿嬤的家族——萬斯珍視的、戰鬥的布蘭頓家族。佐治亞州山間有一些這樣的「羅賓遜」,他們會快活地打獵、釣魚,甚至可能會打起來——特別是在有人違反了山裡不成文的規矩時。
我也是鄉下人,萬斯和我有很多共同點。我們的家庭都是勞工階層——我的父親是一名建築承包商,我的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而我們的祖父母都是大蕭條時期從阿巴拉契亞地區大規模移民到俄亥俄州南部從事工業勞動的人,他的祖父母去了米德爾敦,我的祖父母去了代頓和阿克倫。
最終,成年後我們都離開了我們的根,取得了高等教育學位。他讀了耶魯,我讀了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因爲神在我們的道路上都安排了一個鼓勵努力工作、批判性思維和閱讀好書的人。但是,雖然你可以把男孩帶出農村,但你永遠不能完全把農村帶出男孩的心。
《鄉下人的悲歌》遠不止是口述歷史,它對兩個陷入困境的地域群體進行重要的審視:阿巴拉契亞和鐵鏽帶。這本書值得我們美國人刻意閱讀,認真反思。
同爲鄉下人,萬斯在反思我們的國情和自身背景時,給我留下了很多值得咀嚼的東西。以下是三個初步的收穫。
有不少作者已經簡明扼要地論述了工人階級的焦慮是美國不理智政治環境的核心因素,《鄉下人的悲歌》也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筆觸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我更關心的是教會。對於許多年輕一代的福音派基督徒來說,唐納·川普在老年基督徒中的受歡迎程度既違背了邏輯,也違背了聖經。他的醜惡言語、多段婚姻、輕視女性、對金錢的執著和霸凌的舉止,都讓人對他是否適合擔任國家最高領袖這一職務產生了嚴重的疑問。然而,眾多福音派領袖繼續支持他——不管有多少惡劣的醜聞出現在新聞裡,21世紀福音派對他的虔誠感覺很像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但那個時代的教會急需改革。我並不想說太多,好想要教導你怎麼投票——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好基督徒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我不是要基督徒彼此論斷,但我不希望看到教會的領袖們不加批判地支持某個候選人。
我相信萬斯的經歷對這個問題有一定的啓示。在他的書中,阿嬤經常談到基督教傳統、基督徒責任、神的計劃、神的各樣恩賜,就像許多福音派一樣,然而在下一秒她又像加特林機關炮一樣從口裡噴出大量f開頭的髒字兒來。這就是我們許多南方人在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那種掛名的福音派,一面聲稱「真愛要等待」,一面在威豹樂隊的重金屬搖滾中尋找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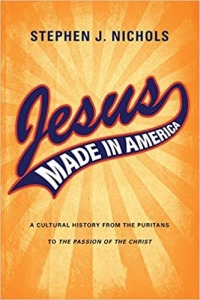 萬斯說,阿嬤的宗教裡有兩個神明:耶穌和國家。但阿嬤相信的更多的是個人主義的耶穌而不是聖經中的耶穌。個人主義的耶穌也就是斯蒂芬·尼科爾斯(Stephen Nichols)在《美國製造的耶穌》(Jesus Made In America)中所說的耶穌:一個感性的個人救主,而不是教會的元首(在阿巴拉契亞的大部分地區,體制性教會並不重要)。這是鄉村音樂中的耶穌,是吉恩·維思(Gene Veith)的《鄉間福音》(Honky-Tonk Gospel)中的救世主——一個道德主義的治療性彌賽亞,在焦慮的長椅上淚流滿面地等待,在鋸木屑小徑上徘徊。這是一個只能賜下恩典,卻不能改變心靈的耶穌,這是一個競選活動常常引用的耶穌。
萬斯說,阿嬤的宗教裡有兩個神明:耶穌和國家。但阿嬤相信的更多的是個人主義的耶穌而不是聖經中的耶穌。個人主義的耶穌也就是斯蒂芬·尼科爾斯(Stephen Nichols)在《美國製造的耶穌》(Jesus Made In America)中所說的耶穌:一個感性的個人救主,而不是教會的元首(在阿巴拉契亞的大部分地區,體制性教會並不重要)。這是鄉村音樂中的耶穌,是吉恩·維思(Gene Veith)的《鄉間福音》(Honky-Tonk Gospel)中的救世主——一個道德主義的治療性彌賽亞,在焦慮的長椅上淚流滿面地等待,在鋸木屑小徑上徘徊。這是一個只能賜下恩典,卻不能改變心靈的耶穌,這是一個競選活動常常引用的耶穌。
這也許是我的阿巴拉契亞足跡與萬斯的最明顯不同的地方。因著神的恩典,我是由愛我的父母撫養長大的,他們的婚姻建立在他們對基督和地方教會的委身之上。我大部分穩定的成年生活都源於在一個沒有戲劇性衝突的家庭中成長,父母委身於彼此、三個兒子和地方教會。
許多在阿巴拉契亞長大的人最終會陷入麻痹性的絕望之中,爲他們父親的罪孽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些父親,就像上百萬首西部鄉村歌曲所唱到的,愛過之後就離開了。萬斯沒有陷入絕望,這很大程度上要感謝他的阿公阿嬤。
如果我們說萬斯克服了驚人的困難從耶魯大學畢業,那已經很輕描淡寫了。他能寫下《鄉下人的悲歌》,正因爲他是個例外。貧窮、暴力(「鄉下人就意味著不知道愛和戰爭之間的區別」)和動盪都在圍繞著他的一生,這就好像出生的時候美國的問題掛在你脖子、成爲你的一部分一樣。
萬斯講述了他身邊不正常的家庭是如何滋生絕望的,而絕望又使許多朋友陷入了藥物濫用和火山般人際關係的惡性循環。
對於許多孩子來說,第一反應是逃跑, 但跑向出口的人們很少選擇正確的門。混亂產生更多混亂,不穩定產生更多不穩定,這就是美國鄉下人的家庭生活。
是的,對於美國鄉下人或者其他類似群體來說,父親缺席、母親獨自撫養孩子是大多數悲劇的原因。我在佐治亞州農村每天都目睹了這一現實,它對我的大家庭產生了不利影響。
 凡是父親和母親在承諾的婚姻中保持共同生活的地方,其他健康的關係往往會發芽。萬斯的生父生母雖然關係破裂,但他阿公阿嬤的愛卻變成了幫助他超越環境的動力。
凡是父親和母親在承諾的婚姻中保持共同生活的地方,其他健康的關係往往會發芽。萬斯的生父生母雖然關係破裂,但他阿公阿嬤的愛卻變成了幫助他超越環境的動力。
正如《鄉下人的悲歌》所揭示的,美國家庭的解體颳起了一股絕望的旋風。這一點在一代年輕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對他們來說,個人責任和以工作謀生是陌生的概念。萬斯講述了一位熟人因爲不想再早起而辭職,然後在Facebook上把自己的困境歸咎於奧巴馬的經濟政策的故事。正如萬斯所說,這就是腐朽選擇的果實,也是其他家庭成員所效仿的選擇。
萬斯承認政府不能解決勞工階層的問題。他是對的,真正的問題遠比缺錢或社會地位低下更深。在本書的最後一頁,萬斯就像耶穌所說「你離神的國不遠了」(馬可福音12:34)的那個文士一樣,用一個具有穿透力的問題痛苦地接近了解決方案:「我們是否能下決心建立這樣的一個教會:迫使像我這樣的孩子能夠與世界互動,而不是在世界面前退縮?」
只有福音才擁有這種力量。
無論你是像我和萬斯這樣的鄉下人,還是你的族譜上裝飾著學者的葉子,我們的根本問題仍然植根於創世記第3章,而唯一真正的解決之道能在羅馬書第3章中找到。萬斯看到了他周圍真正的敗壞(原文直譯):
基督教所描述的墮落世界與我周圍的世界相吻合: 在這裡,快樂的汽車之旅可能很快就會變成痛苦;在這裡,個人的不當行爲會波及到一個家庭和一個社區的生活。當我問阿嬤神是否愛我們時,我請她向我保證,我們的信仰仍然可以讓我們生活的世界變得有意義。我需要一些更深層的正義保證,一些潛藏在心痛和混亂之下的節奏或韻律。
《鄉下人的悲歌》告訴我們,美國南方迫切需要堅強穩固的地方教會。後來,萬斯的生父參加了一個傳講聖經真理的教會,這給家庭帶來了其他家庭所沒有的穩定。
經常參加教會生活的人犯罪率更低,壽命更長,賺錢更多,高中輟學率更低,大學畢業率也比不參加教會的人高。
萬斯正確地將阿巴拉契亞的基督教信仰定義爲 「深沉的宗教情感,但對真正的教會團體沒有任何關聯」,這可是不小的問題。
在結尾處,他思考「像我們這樣的人是否能真正得著改變」。人類政府,無論多麼有限和富有同情心,都會在成爲救贖手段這件事上失敗——歷史的垃圾箱裡排列著無數的國家見證了這一點。萬斯說,「我仍在探尋那幾年前已經丟棄了的基督信仰」,我爲他禱告,希望他繼續在這個方向上努力。歸根結底,古舊十架是唯一可以發生真正改變和找到持久喜樂的地方。
作爲教會領袖,我們至少有四種方法可以回應萬斯所描述的災難。
說起來,《鄉下人悲歌》是生硬的,赤裸裸的,並且(讀者請注意)充斥著R級語言,但也很難有其他方式寫下這樣一本書。歷史就是生硬的、赤裸裸的,充滿了R級的東西,也許很多人的個人故事也同樣殘酷。萬斯寫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殘酷誠實的回憶錄,這本書解釋了很多美國文化中的分裂和絕望,並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揭露了我們最深層的需要——通過福音的力量進行內在的轉變。
《鄉下人的悲歌》是一個引人入勝、寫得漂亮的關於真理和恩典的寓言。真理揭露了我們國家數百萬人鮮爲人知、令人震驚的絕望生活;恩典則表明神不受我們的環境限制,他能用彎曲的杖畫下漂亮的直線。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illbillies: My Kinsfo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