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時讀的大多是非虛構作品。這種習慣,多少也是被現實推著走的。作爲地方教會的一名長老,我需要教主日學,常常要查閱各種聖經註釋和學術著作,好把經文講清楚。作爲福音聯盟的編輯,我也會盡量閱讀我們評介的書,甚至包括一些最終沒有寫書評的作品。除此之外,非虛構寫作也滿足了我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好奇心。無論是工程、政治,還是歷史,只要是深入探討的內容,我都很感興趣。
不過,說到理解一些複雜的哲學思想,小說有時反而更有幫助。我至今仍會推薦比爾·沃特森(Bill Watterson)的《卡爾文與霍布斯》(Calvin and Hobbes)漫畫,作爲理解後現代主義的一把鑰匙。有時候,一個小男孩和他那隻毛絨老虎,比成年人板著臉講理論,更能把那些觀念的荒謬之處暴露出來。C. S. 路易斯(C. S. Lewis)在〈藍鏡與球面平民〉(「Bluspels and Flalansferes」)一文中正是這個意思。他寫道:「對我來說,理性是認識真理的工具;而想像力才是理解意義的器官。」小說正是通過塑造我們的想像力,用生動的隱喻,把抽象的思想變得具體。
2025 年,《刷屏至死:在數字時代重拾真實人生》(Scrolling Ourselves to Death: Reclaiming Life in a Digital Age)一書的多位作者,曾推薦過不少非虛構作品,幫助基督徒反思自己與科技之間的關係。這些書對當代社會的問題給出了清晰而有力的診斷。但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七部小說,也許能在更深的層次影響我們的想像力,推動我們思考:什麼才是人之爲人的本質?科技究竟應該服務什麼目的?其中大多數是反烏托邦小說,意在發出警告。這一點,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如果是在幾年前,我大概還會說,路易斯的《宇宙三部曲》長期以來被嚴重低估。但近些年,這套作品重新引起了不少關注,讚譽也明顯多了起來。它或許永遠無法達到《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那樣的普及度,但在神學與社會批評層面,《宇宙三部曲》同樣有著強大的穿透力,引導讀者直面基督教世界觀所宣告的客觀真理。歷史學家莫莉·沃森(Molly Worthen)就在 2023 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這套科幻小說在她的信主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亞馬遜介紹這套書說:
亞馬遜介紹這套書說:
路易斯的《宇宙三部曲》創作於二戰前夕及戰火最黑暗的歲月中。
它與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一樣,都是跨越時代的經典之作。
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深愛這部作品,既因爲它精彩絕倫的故事本身,也因爲它所關切的道德問題意義深遠。
作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黑暗之劫》是他的隨筆〈圈內人〉(「The Inner Ring」)和教育系列講座《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的小說版。路易斯把「無胸之人」這一概念用故事的形式呈現出來,讓讀者看到:當赤裸裸的唯物主義科學排擠掉神學與道德關懷後,最終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如今,我們看到了一些關於人工智能與某種邪靈力量相關的理論,而路易斯在書中描繪的場景頗爲耐人尋味:超自然力量往往就藏在科學自然主義的幕布背後。我們都應該多讀一些路易斯的作品,《黑暗之劫》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與科技的關係,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洞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這部小說出版於 2021 年。憑他的聲望,這本書登上暢銷榜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它真正值得被廣泛閱讀的原因,並不只是作者的名氣,而是它本身講了一個好故事,而且講得極好。書中展望的未來世界裡,基因改造兒童已是常態,機器人則充當孩子們的「具身化」人工智能夥伴。這樣的未來,似乎每過一個月就離我們更近一步。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計劃於 2026 年上映,定位是反烏托邦科幻片,對此我毫不意外。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這部小說出版於 2021 年。憑他的聲望,這本書登上暢銷榜幾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它真正值得被廣泛閱讀的原因,並不只是作者的名氣,而是它本身講了一個好故事,而且講得極好。書中展望的未來世界裡,基因改造兒童已是常態,機器人則充當孩子們的「具身化」人工智能夥伴。這樣的未來,似乎每過一個月就離我們更近一步。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計劃於 2026 年上映,定位是反烏托邦科幻片,對此我毫不意外。
這本書內容很難概述,因爲稍不留神就會劇透太多。故事從克拉拉的視角展開,她是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夥伴。隨著情節推進,我們見證了克拉拉日漸覺醒的意識和逐漸豐富的性格,也看著她與主人喬西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與此同時,喬西的母親有一個令人心碎的計劃,如同烏雲般籠罩著整個故事。雖然開頭節奏較慢,但《克拉拉與太陽》讓人慾罷不能,因爲它迫使讀者直面一些艱難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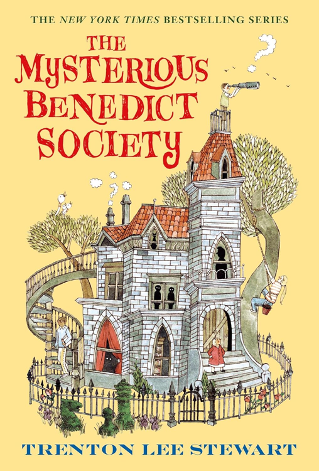 《本尼迪克特先生的神祕社團》出版於 2008 年,那時我們還沒有體驗到無處不在的智能手機所帶來的全部焦慮。儘管如此,斯圖爾特已經敏銳地指出了威脅每個人心理健康的東西:書中稱之爲「緊急狀態」(The Emergency)。這是一部兒童小說,講述了四個天才少年如何聯手阻止一個征服世界的陰謀。
《本尼迪克特先生的神祕社團》出版於 2008 年,那時我們還沒有體驗到無處不在的智能手機所帶來的全部焦慮。儘管如此,斯圖爾特已經敏銳地指出了威脅每個人心理健康的東西:書中稱之爲「緊急狀態」(The Emergency)。這是一部兒童小說,講述了四個天才少年如何聯手阻止一個征服世界的陰謀。
與我們這個被媒體淹沒的時代格外契合的是,書中的世界征服計劃不是通過軍事力量,而是通過製造焦慮,迫使人們把權力拱手讓給一個貌似仁慈的官僚獨裁者。
斯圖爾特的整個系列都很值得一讀。故事詼諧有趣,內容健康向上,善惡分明。而且,與許多童書不同的是,書中有值得信賴的成年人,他們不只是一些笨拙配角,只是爲了襯托小主人公們的能幹。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傳達的信息很清楚,卻不流於說教:電子媒體在塑造人心方面有著強大的力量,而我們往往渾然不覺。如果你想和孩子討論媒體的潛移默化之效,這本小說是很好的切入點。
 對許多高中生來說,閱讀奧威爾的這部經典反烏托邦作品,是一種「成人禮」式的必經體驗。自 1949 年出版以來,書中那個屏幕無處不在的監控社會只變得越來越真實。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我們自願參與了對自己的電子監控。
對許多高中生來說,閱讀奧威爾的這部經典反烏托邦作品,是一種「成人禮」式的必經體驗。自 1949 年出版以來,書中那個屏幕無處不在的監控社會只變得越來越真實。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我們自願參與了對自己的電子監控。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出版《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時,認爲西方文化已經變得更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但有時我覺得,我們不過是把兩個世界最糟糕的部分挑出來,拼湊到一起。
人們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一九八四》中以國家爲中心的監控與宣傳機制上,這會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有言論自由權利的美國就能高枕無憂。然而,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中,言論管控和歷史修正主義的企圖屢見不鮮,其程度有時甚至令人聯想到奧威爾筆下的強制壓迫。如果把他的小說與凱·施特里特馬特(Kai Strittmatter)在《我們已被和諧》(We Have Been Harmonized)中對當代中國監控體系的描述對照來讀,應該會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究竟是在多麼心甘情願地邁向一個全面數字化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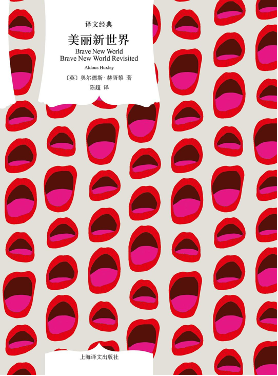 使用迷幻藥物、研發人造子宮、人類胚胎基因工程——赫胥黎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每個月都在變得更加真實。
使用迷幻藥物、研發人造子宮、人類胚胎基因工程——赫胥黎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每個月都在變得更加真實。
我們採用新技術時,往往只想到它們的好處。汽車讓我們能更常與家人團聚,手機能在緊急情況下救命,人造子宮可以挽救早產兒。但這些技術往往也帶來負面影響。比如赫胥黎所展示的:當性與生育分離,當孕育與養育脫鉤,就會催生出一個人命不再珍貴的社會。
當把孩子的基因來源與孕育過程中的親密聯結分開變得越來越容易時,《美麗新世界》應該促使我們思考:當我們的後代是「製造」出來而非「生養」出來時,我們將失去什麼。赫胥黎的小說能引導讀者回到聖經,去思考人之爲人意味著什麼,以及這應當如何塑造我們在生育問題上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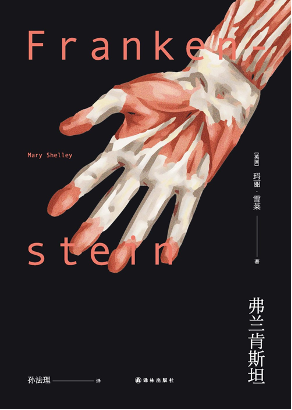 自 1818 年出版以來,維克多·弗蘭肯斯坦和他創造的怪物的故事已被改編過數百次。對許多人來說,一提到這部小說,腦海中就會浮現 1931 年電影版中鮑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飾演的怪物形像。更偏文學研究的讀者,則可能會想到這部作品對哥特小說傳統的影響、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因性別而不得不匿名出版的事實,或她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雪萊(Percy Shelley)之間的關係。
自 1818 年出版以來,維克多·弗蘭肯斯坦和他創造的怪物的故事已被改編過數百次。對許多人來說,一提到這部小說,腦海中就會浮現 1931 年電影版中鮑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飾演的怪物形像。更偏文學研究的讀者,則可能會想到這部作品對哥特小說傳統的影響、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因性別而不得不匿名出版的事實,或她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雪萊(Percy Shelley)之間的關係。
然而,《弗蘭肯斯坦》最重要的一個線索,就藏在它的副標題裡:「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在希臘神話裡,普羅米修斯創造了人類,並把火帶給他們,由此開啓了技術進步的大門。這個故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作爲照著上帝形像被造的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當技術被推向極限時,那些不受歡迎、卻往往無法預料的後果,又將如何反噬我們自身?
 不要因爲克萊頓的小說催生了一個電影系列,就低估了《侏羅紀公園》的文化意義。小說中的評論比電影發人深省得多。與續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不同,這部 1990 年的驚悚小說遠不止是一本讓人慾罷不能的消遣讀物,它更是對人類在技術和生命面前狂妄自大的有力揭示。
不要因爲克萊頓的小說催生了一個電影系列,就低估了《侏羅紀公園》的文化意義。小說中的評論比電影發人深省得多。與續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不同,這部 1990 年的驚悚小說遠不止是一本讓人慾罷不能的消遣讀物,它更是對人類在技術和生命面前狂妄自大的有力揭示。
有人問登山家喬治·馬洛裡(George Mallory)爲什麼他要攀登珠穆朗瑪峯,據說馬洛裡的回答是:「因爲它就在那裡。」1999 年,人們發現了他的遺體,證據顯示他從未登頂。我們這個時代對待技術的方式往往與此如出一轍:我們採用新技術,把它們應用到新的領域,僅僅是因爲這種可能性存在。
在努布拉島(Isla Nublar)上的侏羅紀公園裡,約翰·哈蒙德(John Hammond)試圖通過基因工程製造並圈養恐龍,由此引發的混亂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對待技術創新態度的生動寫照。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約翰·哈蒙德們很少被自己的造物吞噬。那些怪物更常吞噬的,是那些只想來看熱鬧的無辜之人。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7 Novels to Help You Think About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