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馬克·科默(John Mark Comer)的著作《踐行這道:與耶穌同在、效法耶穌、行他所行》(Practicing the Way: Be with Jesus. Become like Him. Do as He Did)被評爲 ECPA 2025 年度基督教圖書。許多福音派基督徒正在討論書中對屬靈生命塑造的構想,這並不出人意料。那麼,我們是否需要更多地與科默的作品對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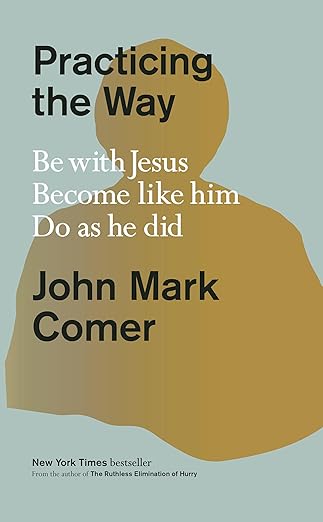 首先,人們對他的方法既充滿興趣又頗感不安,這現象本身就說明了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與不少基督徒交流,他們普遍覺得科默的靈性塑造方式有些不妥,卻又說不清具體原因。這種張力值得我們認真進一步思考。
首先,人們對他的方法既充滿興趣又頗感不安,這現象本身就說明了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與不少基督徒交流,他們普遍覺得科默的靈性塑造方式有些不妥,卻又說不清具體原因。這種張力值得我們認真進一步思考。
其次,科默的方法與改革宗理解的屬靈塑造之間的差異確實值得探討。科默的書影響了許多福音派人士,而福音派運動本身正是源自十八世紀復興時期的改革宗傳統。可惜我自己的那本討論改革宗靈性塑造的書,因出版流程已進入後期階段,無法直接與科默的觀點展開對話。
這篇文章並不是一本書評。我真正想做的,是指出《踐行這道》有三個關鍵之處偏離了宗教改革家(我認爲聖經本身)所倡導的靈性塑造模式。
改革宗傳統堅持:唯有因聖靈重生並與基督聯合的人,其屬靈生命才可能成長。脫離這種救贖性的聯合,成長便無從談起。因爲惟有當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他才能成爲我們的「公義和聖潔」(林前 1:30)。耶穌明確教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 3:3)。
然而,在《踐行這道》中,重生和與基督聯合的教義幾乎完全缺席。科默確實談到聖靈的重要性,並說屬靈塑造需要你「藉著聖靈安居在耶穌的同在中」(37 頁)。但他並沒有解釋人如何得到聖靈的幫助;在書中也看不到任何跡象表明,聖靈使人重生是一個清晰而決定性的時刻,而正是藉著這個時刻,神「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 1:3)。
相反,科默把焦點放在成爲耶穌的「學徒」上,把他視爲最偉大的拉比,目標是成爲一個能「說耶穌所說、行耶穌所行的那類人」(122 頁)。這樣的描述雖以耶穌爲中心值得肯定,卻忽略了聖靈促成的我們與基督的聯合。科默的整套方法基本上圍繞著:耶穌在地上的事奉爲我們留下了一個可效法的榜樣。效法基督確實是一條明確的聖經主題(如彼前 2:21),但在理解基督是誰、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時,這並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主題。
當我們過度強調「耶穌作爲榜樣」這個主題時,便會遮蔽一個聖經真理:我們首要的、根本的需要不是道德導師,而是救主。聖經教導說,「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約壹 5:1)。這意味著,沒有「從神而生」的人,根本無法相信耶穌是基督,也就不可能在屬靈生命上有任何成長。比如,甘地雖然從耶穌的道德榜樣中得到啓發,但顯然他從未悔改歸信,最終仍然死在罪中。
宗教改革的核心,正是要恢復「以神的話語爲中心」的敬虔生活。改教家們堅信,唯有不斷深入研讀神的話語,才能真正推動靈命成長。他們也教導,任何靈命塑造的方式都必須源自聖經、倚靠聖經。正因如此,許多中世紀信徒習用的靈性塑造方法被捨棄,轉而回歸《詩篇》119:9 所啓示的樸素真理:「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爲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科默在《踐行這道》中,將讀經列爲個人「生活準則」(Rule of Life)中必須納入的九項核心操練之一(181 頁)。他也寫道,「聖經是我們『藉著心意更新而改變』的主要途徑」(186 頁)。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首先,讀經不該只是「耶穌門徒用來塑造靈性」的眾多方法之一(181 頁),而是我們與神相交的根本途徑。正如神學家巴文克所說:「聖經是連接天國與塵世的永恆紐帶。」
但科默卻將「更多查考聖經」稱爲「注定失敗的策略」,並認爲「做禮拜、聽精彩講道、定期查經......在大規模群體中通常難以帶來真正深刻的改變」(86-87 頁)。他一方面肯定講道和查經「不僅有益,更是必需」(86 頁),另一方面又斷言單靠這些「遠遠不足以」促進靈命成長(87 頁)。
這種論調令人想起中世紀教會的做法——他們表面尊崇聖經,卻在實際操練中認爲神的話語不夠用。當時教會主張,真正的靈命突破要靠各種附加的儀軌修行。但對秉承改革宗精神的基督徒而言,神的話語始終是我們敬虔生活的核心。聖經既是改變生命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屬靈成長的藍圖。
科默在《踐行這道》中展現的神學立場兼容幷蓄,導致神學立場不夠清晰。他將神學傳統迥異甚至彼此對立的著述混爲一談,卻對其中的矛盾輕描淡寫。雖然他偶爾也會引用改革宗的思想家如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羅莎莉亞·巴特菲爾德(Rosaria Butterfield)、提姆·切斯特(Tim Chester),但他更多依賴的是天主教作家(聖女大德蘭 [Teresa of Ávila]、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盧雲 [Henri Nouwen])、東正教作家(卡利斯托斯·維爾 [Kallistos Ware]、卡利斯托斯·卡塔菲吉奧蒂斯 [Kallistos Katafygiotis])、貴格會神祕主義者(托馬斯·凱利 [Thomas Kelly]),甚至還有非基督徒靈性作者紀伯倫(Kahlil Gibran)。
他將這些背景各異的思想家統稱爲「耶穌之道的大師」(47 頁),暗示這些「靈性大師」(43 頁)雖然來自不同傳統,卻是殊途同歸。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比如他在書中引用天主教作家論及「聖體聖禮(Blessed Sacrament)」時,僅輕描淡寫地提上一句「即新教徒所說的聖餐」(42 頁)。然而對聖禮理解的根本分歧,正是宗教改革時期的核心爭議。更諷刺的是,在同頁他又引述貴格會凱利的觀點,而這個流派恰恰以完全放棄外在聖餐儀式著稱。科默從未提醒讀者,這些「耶穌之道的大師」(43 頁)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神學衝突。
這種兼收幷蓄的後果,就是構建出一套在基督教歷史上找不到確切淵源的靈性塑造體系。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科默對東正教作家威爾《東正教之路》(The Orthodox Way)的推崇,科默寫道:「我讀這本精彩絕倫的書時,就彷彿回到了家」(237 頁)。
但《踐行這道》既沒有東正教對聖像的崇敬,也缺乏對「天主之母」(Theotokos)馬利亞的尊崇,更不見使徒統緒的祭司職分——而這些恰恰是東正教靈性塑造的支柱。如果他讀《東正教之路》真有「回家」的感覺,那爲何他沒有加入東正教會?部分原因恐怕是:一旦他真正扎根於某個具體傳統,他就無法繼續維持自己這種自助餐式的靈性塑造模式了。
科默爲基督徒生活勾勒的藍圖,本質上是一種「隨意挑選」的自助餐式方法。這並不是指他暗地裡是天主教或東正教的擁護者、卻刻意隱瞞自己的立場,而是說這種模式缺乏穩固根基,難以融入任何既定的基督教傳統。
與此相比,改革宗的靈命塑造強調完全、一致地以聖經爲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正是這種堅實的聖道根基,歷經數世紀考驗,始終保持著連貫性與生命力。
只要改革宗確實正確理解了聖經,《踐行這道》在屬靈塑造方面就代表了一種明顯偏離聖經的方式。正如科默對「重生」和「與基督聯合」主題的輕描淡寫所顯示的那樣,只要屬靈塑造不扎根於聖經,它就會隨著時代中看似吸引人的各種神學潮流四處漂移。
就改革宗傳統對聖經的正確理解而言,《踐行這道》顯然偏離了符合聖經的靈性塑造觀。從科默淡化「重生」「與基督聯合」等核心教義可以看出,一旦靈命塑造脫離聖經錨點,就難免隨波逐流,追逐當下流行的神學風潮。
或許科默與其他一些人對福音派的宗教改革傳統已經感到不滿,想要徹底擺脫它。決定在他們手裡。但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就應該清楚地說出來,並坦然承擔這個選擇的後果。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Problem with Comer’s Cafeteria Approach to Spirituality.